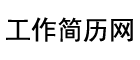渡边恒雄的个人简介
渡边恒雄1926年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考进了《读卖新闻》报社。后任日本最大报业集团《读卖新闻》的总裁和主笔。渡边恒雄在日本政坛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被称为“一代政治记者”、“终身主笔”。渡边恒雄反对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致力于揭露日本的战争历史。
人物简介
在日本现当代史上,就作为新闻记者、报人的资历和影响而言,堪与著名政治记者、《读卖新闻》老板兼总主笔渡边恒雄(Tsuneo Watanabe)相匹敌者鲜,恐怕只有战前《朝日新闻》社长兼主笔绪方竹虎和曾担任过《东洋经济新报》社长的石桥湛三,但后两位均在战后跻身政界,成为政治家。而只有渡边恒雄以普通“番记者”(日本新闻界独有的现象,指长期专门跟随政界某个特定人物、随时采访以获取即时的一手消息的新闻记者)入行,从驻美特派员而政治部长,从编辑局长到执掌社论的编辑委员、总主笔,从而成为报纸发行量冠全球之首(1400万份),旗下拥有电视台、出版社、职业棒球队及众多广告媒体的传媒王国读卖集团的社长,可谓媒体人的“最高境界”。但光环笼罩之下,渡边本人最看重的却是总主笔的名头,被称为“一代政治记者”、“终身主笔”。 渡边恒雄是日本尚健在的前辈新闻工作者中,为数极少的经历过战争的人。1945年6月底,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一周后即被征召入伍,属于“学徒出阵”的一代。出发时,渡边偷偷往行囊中塞了三本书,分别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威廉?布莱克诗集》和研究社版《袖珍英语词典》。渡边幼年丧父,人生态度比较虚无,是哲学青年,他觉得“反正要到战场上送命,真能扛得住的只有哲学”,于是囫囵吞枣读了很多康德、尼采,还有日本的西田哲学(日本现代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京都学派创始人),但后者“没什么用”。跟他差不多同时接到征召令的一名东大法文科的友人,正吃着饭团,听渡边说了句“战场上也是有诗的”,愣了一下,饭团就掉到地上。原来,他把“诗”理解成了“死”(日语中,“诗”与“死”同音)。这对渡边来说似乎是一个隐喻,“原来应征入伍是与死相连的。”不过,幸运的是,日本旋即投降,渡边也免于在海外战场上当炮灰的命运。
随后,复学东大;出于对战争和天皇制的痛恨,加入日共,后又被除名。渡边作为政治记者最初的修炼,是跟随自民党政治家大野伴睦(Banboku Ohno,1890-1964,岐阜县山县市出生,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肄业。自民党实力派政治家,历任北海道开发厅长官、众议院议长、自民党副总裁等)的番记者,深蒙后者信任。对渡边而言,大野是父兄般的存在。正因了大野,这位自民党早期资深政治家,田中派之前最富实力的派系大野派领袖的青睐,渡边才得以近距离深度观察日本的政治生态,尤其对执政党内派系斗争的游戏规则和潮流颇有心得。
作风故事
日本新闻界实行记者俱乐部制度,各大媒体派到总理府、政府各大机构(省厅)和相关政治家身边工作的记者有配额限制,但由于媒体发达,规模庞大,在一些大牌政治家身边工作的番记者经常有一群人。政治家出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好恶,不可能对所有的媒体和记者“一碗水端平”,有限的信息资源往往优先、定向流入部分媒体。这在日本是人之常情,记者同行之间也彼此见怪不怪。晚间,大野家的客厅里动辄有十数名番记者,盘坐在榻榻米上,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一边等消息。大野其人性喜风流猥谈,段子一个接一个,包袱连甩不断,兴致好时,动辄侃上一个时辰。记者们很怕这个,再生动的段子,听过十遍,也腻了,于是拍屁股走人。渡边也起身佯装告辞,跟最后一拨记者一起作鸟兽散之后,再独自悄然折返。绕过正门,翻墙而入,径直走到女仆跟前:“请把老头子叫来。”于是,俩人切入正题。
喜欢段子的政治家不止大野,有名的还有前首相岸信介。如果说,大野的段子是某种旨在抖包袱的诙谐猥谈的话,岸信介的段子才是真正的浑段子,即兴、直接而生猛。对这种应酬,渡边乐此不疲,接招还招,起承转合,每每扮演捧哏角色。为此,屡遭记者团抗议:“渡边,够了。每次都因为你和岸先生的二人转,害得大家采访交不了差。”
作为跟随大野的番记者,渡边婚后选择在离大野宅邸咫尺之遥的地方赁屋而居,白天到大野府上报到,晚上陪酒成了日课。作为政治记者,渡边影响力日增,不仅深度介入派阀政治,有些派内重大决策,干脆由渡边代为向记者团其他媒体同行们发表,事实上扮演了派阀大佬军师的角色。前首相池田勇人的秘书伊藤昌哉在其著作《渡边恒雄:媒体与权力》中说:“大野是如何决策政治行动的呢?只需对其意志决定路径加以梳理便会发现,在最后的环节都会触到渡边。渡边不仅作为大野的耳、目收集信息,而且发挥了作为脑,即指挥塔的作用。”这在后来成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的入阁问题上,表现尤为充分。
在日本政界,青年政治家成功的龙门是入阁,尽可能多地出任各种重要阁僚或党内要职,积累经验和人脉、金脉,为自己做大,最终通向王者之路作铺垫。作为政坛青年才俊,中曾根虽然29岁就当选国会议员,但由于系党内少数派河野派成员,入阁之路迢迢。于是,渡边在一家高级料亭设局,安排身为党的副总裁,同时兼河野派组阁窗口的大野与中曾根见面。谁知两人一见,大野劈头就指中曾根骂道:“就是你小子在造船疑狱事件(围绕旨在降低造船事业中的贷款利率的《外航船建造利息补给法》的制定请愿问题而发生的收受贿赂案件。1954年1月,东京地方检察院以强制调查司法介入,政财两届多名要人被卷入,也成为吉田茂内阁被倒阁的动因之一,是战后政治的污点。后著名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以事件为背景出版了一部小说《日本的黑雾》)时的预算委员会上说u2018大野伴睦接受了贿赂,我敢拿政治生命打赌u2019的话吧?那时的一剑之仇,老子可还没忘呢!”渡边见势不妙,出来打圆场说:“副总裁好一个直性子。但对过去的事情,不磨磨唧唧纠缠不休是谁说的来着?造船疑狱事件那会儿,中曾根还在在野党改进党那边。记恨人家在野党时代的发言,这会儿旧话重提,不太像副总裁吧?”一番话,使僵硬的空气顿时缓和。大野说:“嗯,也是,知道了。不过,中曾根君,你是有总裁相。”渡边顺水推舟道:“中曾根因系河野派,远离入阁窗口,无法施展。身为副总裁,您有河野派的推荐权,无论如何请协助推进中曾根的入阁事宜。”一句话,1959年6月,中曾根成了河野派中唯一入阁的成员,出任岸信介第二任改造内阁的科学技术厅长官,时年41岁。而大野那句“总裁相”云云的话,让渡边大吃一惊。中曾根后来在政坛的发迹,也反证了大野识人的眼力。
中曾根入阁后,有一天叫渡边去他办公室,拿出一叠厚厚的文件――关于造船疑狱事件的检方调查报告:“我的高中同学是此案的担当检察官,偷偷把材料给了时为在野党的我。”渡边随手翻了翻,里面有张手绘的草图:在某间料亭的单间,大野伴睦坐在什么位置,与事件有关的其他人坐在什么位置,艺伎坐在什么位置,一清二楚。中曾根根据检方的调查结果,在把金钱授受关系摸了个底掉之后,才在国会上对大野出手。对少年气盛的中曾根来说,当着代表新闻界的渡边的面,痛遭一通狗血淋头,可为入阁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地给人家赔不是,无异于胯下之辱。所以,特向渡边陈请:“彼时的攻击完全是本着实事。这点务必请渡边你了解。”
此事堪称渡边与政坛后起之秀中曾根互为盟友、“蜜月”绵绵的契机。同时,也使渡边更清楚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及外交战略等政策性考量,其实并不是绝对的。人在厕身权力斗争时,诸如憎恶、嫉妒及自卑感等情感性因素,往往会起更大的作用。”
另一位渡边过从甚密的政治家是田中角荣。作为政治记者,出于职业性的敏锐嗅觉,渡边对田中曾抱有莫大的期待。战后,从吉田茂开始,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历任首相无一不是官僚起家,其政权也有很强的官僚政权色彩,令人窒息。只有田中,这个没有大学文凭、靠建筑业致富、38岁即成功入阁的“黑马”,可能成就一番“党人政治”的大业,以涤荡官僚政治的保守和暮气。彼时,渡边刚结束在华盛顿支局四年的特派员生涯,回到国内,便马上投入到“角福战争”(媒体对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之间党总裁和首相宝座争夺战的称呼)的相关报道活动中。
从性格取向和对政治实力的判断上,渡边无疑是田中的拥趸:“角先生(媒体人对田中角荣的昵称)什么都跟你说,非常坦诚,是情报之泉。且他讲话非常有趣。他要是东大法学部毕业的话,绝对当不了总理大臣,充其量也就是哪个省厅的次官,或者开发银行的总裁之类的。”
1965年,田中任自民党干事长,离总裁的宝座还有一步之遥。包括渡边在内,一些大报的政治记者每天晚上都往田中家跑。田中重乡情,重义气,每天接见的几十号人中一半以上来自家乡新馈U庠诙┏錾⒈弦涤诙蟮拿教寰⒍杀呖蠢矗渴粝沟⑽蠊し颉V沼谟幸惶烊涛蘅扇蹋蕴镏兴担骸按筇迳希窍壬丫歉墒鲁ぃ乱徊绞且晌芾碜懿玫娜耍刻炷讣甘谧酉绨屠校床患颐切挛偶钦撸馑闶裁词拢俊倍焙鹤犹镏幸幌伦泳突鹆耍骸跋绨屠惺鞘裁椿埃慷杀撸愀沂栈兀 倍杀咦灾砜鳎苍谄飞希硎疚薹ㄊ栈亍L镏懈昊鹆耍骸澳愀缮婺谡±献酉爰敫陕铮疚以敢狻D阈∽用看喂矗也灰舶敫鲋拥恪⒁桓鲋拥愕馗懔穆穑亢问钡÷悴怀桑俊碧镏兴档牡娜肥鞘率担1叱栽绮捅吒杀咛富啊5谡庵洲限蔚姆瘴е校杀咦遭庖膊荒艿舸笈疲阕煊菜挡皇窃谀米约核凳拢恰霸谒邓行挛偶钦叩氖隆保低赉肴ァ:罄矗杀咛镏忻厥樵幺嗝担骸敖窍壬担嫦胱岫杀吣切∽右欢佟!钡镏胁患浅穑鹿ゾ退阃炅恕
田中角荣如果不是战后日本金权政治始作俑者的话,至少也是集大成者。靠政治献金的推动,广罗党羽,使田中派成为党内最大的派系,历久不衰。不仅如此,政治与建设业者的利益粘连孕育了“建设族”、“道路族”等利权结构,历来是日本黑金政治的渊薮。不久前,因卷入西松建设非法政治献金案而备受舆论指责的日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就曾经是昔日田中门下的弟子。对此,长年在政治漩涡中呼吸、深谙派阀政治游戏规则的渡边自然再清楚不过:“当了政治家,从大佬那儿拿钱。拿了钱,等自己也具备敛财能力之后,再分给下面的小的们。在当时的政界,这是铁则。虽然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随着《政治资金规正法》的强化,报纸也拼命抨击金权政治,最近情况似乎没那么严重了,固然是好事,但我不认为这种陈规已完全绝迹。”
但纵然如此,对同行立花隆以那种极端的形式在《文艺春秋》上曝光,渡边本人持保留态度。这里既有立法方面的问题(原有的《政治资金规正法》在1975年修正前,对于政治活动捐助的法律规制极其宽泛),也有合法性资金被舆论曝光后的社会效果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是具有违法性的、会成为刑事案件的聚财方法的话,报纸和电视本不应曝光”。
对田中大佬其人超乎常人认知与想象的敛财、散财方式,渡边在回忆录中多有披露,有些是从未公开过的材料:据《朝日新闻》记者三浦甲子二透露,原NHK节目主持人、参院议员宫田辉怀里抱着个大纸袋从田中家出来,与正要进门的三浦在玄关撞了个正着。宫田吓一跳,纸袋掉地上,一捆捆的纸币散落出来,“大约有3000万日元左右。”宫田慌了神,也不顾打招呼,低头拾起钞票,装进纸袋,夺门而逃。与渡边一样同为见多识广的大报政治记者的三浦,也不禁在心里感叹道:“到底是角先生,玩的活就是大,跟我们通常听到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啊。”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在田中的连载专栏(《我的履历书》)结束,结集成书后,去府上拜会,因为田中表示个人要购买出版的相当册数。“角先生打开大保险柜,啪啪几下就拿出200万日元。当然全都是正当的购书款。”当记者要开收据时,角先生说:“那玩意不必。”记者偷偷瞄了一眼保险柜,“里面密密实实码放着成捆的钞票,堆得跟报社的稿纸似的。”因法律规制等方面的原因,日本政治资金有一个特点:现钞主义。不是现钞,全无效果。“拿的是现钞,递的也是现钞,所以踪迹全无。”
1976年,随着洛克希德事件(1976年2月,因美国上院多国籍企业小委员会上的证言而被新闻界曝光的航空业界黑金事件,系日本战后四大丑闻之一。美洛克希德公司通过对日本政府高官行贿,变更了全日空公司从美国采购的飞机机型。事件导致田中角荣政权下台,田中角荣及其秘书、前运输大臣及次官、全日空、丸红公司高官多人被起诉。一审、二审判决有罪。)被媒体曝光,已于两年前“退阵”的田中因受贿和违反外汇管理法嫌疑被捕。这是战后由吉田(茂)、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一路开创的、被称为“保守本流”的保守政治的最大危机。本来此前围绕“保守本流”的是非存废,政坛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势力,始终在较劲。但此时,两种力量突然联手,矛头一致对准拿洛克希德事件开刀的首相三木武夫,旨在“倒三木”的“举党体制”迅速形成,连此前最大的反田中派福田赳夫也加入其中。
至此,现代日本的政治机器开始在与道德不同的坐标下运转,田中被捕后,其评价反而上升,舆论和政界的同情明显向田中倾斜。从当时的主流民意来看,逮捕前首相的做法,无论如何有些“过了”。这里,日本社会心理中保守性的一面再次浮水:国民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有时可超越道德律法,更看重现实的游戏规则。
田中果然“有种”,在拘留所里无论检方百般质询,誓死不吐一字。一个月后,被保释。最后,在有罪终审判决之前病殁。田中其人到底是不是一块“善玉”另当别论,但其继承和主导的“保守本流”的政治成色,至今仍是日本政坛的背景主色调则是不争的事实:直到其因脑梗塞病倒、丧失语言和行动能力的1985年,田中一直是政坛的幕后操盘手,不折不扣的政治枭雄、“造王者”(King Maker);直到今天,源自前身田中派的町村派,仍然是自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系。
作为日本尚健在的头号大牌政治记者,渡边与战后历届首相及实力派政治家均有过从,可谓阅人无数。同时,政界人脉多多,从政机会数不胜数。经他介绍,做政治家、甚至首相秘书官的记者同僚、部下有之;前首相三木武夫也曾说服其弃纸(报纸)从政。况且,渡边其人对政治本身并无“洁癖”,至少不讨厌。但他在长达60年的政治记者生涯中,却始终未曾有过“下水”的冲动,真正做到了“常在河边走,从来不湿鞋”。一般人会以为,这需要极大的定力。但对“新闻原教旨主义者”渡边来说,则未尝不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在渡边心中,甚至连世界第一大报《读卖新闻》社长的位子都无所谓,“只要能将主笔进行到底。生涯,只想做一名新闻记者。”
对被称为传媒社会的日本而言,新闻界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单纯的旁观者、报道者和评论者,在某种意义上,其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游戏的参与者。渡边恒雄作为政治记者的言动,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远的不提,从几年前,针对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罔顾对中韩外交的失政、恶化,一再偏执于靖国参拜的问题,与《朝日新闻》主笔若宫启文(Yoshibumi Wakamiya)长篇对话,指小泉作为政治家“没有教养”,到两年前做局,撮合前首相、自民党总裁福田康夫和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实现峰会,动议朝野两党保守联合,日本媒体大力介入现实政治操作,以舆论本身来诱导、酿造舆论的主动投球的激进姿态令人印象深刻。
也许,正因了这种显赫一世的权力,洞若观火如渡边恒雄者才宁愿放弃现实政治中“王者”宝座的逐鹿游戏,而甘愿做“无冕之王”,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