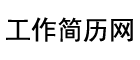陈开平(作家)的个人简介
陈开平,笔名:曙光,陈说,祖籍河南颍川,1965年出生于江苏省沛县。
人物履历
作家,现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1999年先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北京大学,先后做过记者、编辑、副主编、策划总监等。主要作品有《凝》、《小河》、《风向》、《故乡的秋》、《祖母的故乡》、《云 叶子 麦地》、《父亲的季节》等,其《他们的村庄》编入中国当代散文精选。1992年来先后有40余篇作品获奖,被人誉为具“后现代主义”作家,现就职于北京某杂志社。
尽管陈开平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经历了“文革”的洗涤,进而又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给少年的他集结了很大的身心财富,他是父亲、母亲的最小的孩子,母亲43岁才有了他,残酷的生活环境和“内省”的自我压力给陈开平的创作奠定了厚重的基石。他不得不边干农活、边卖线、边卖西瓜边写作。。。。。长期生活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差相碰撞的环境下,使他的作品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玛瑙樱桃,在现实和情感的双重映照中折射出超然的和谐、健康而又令人神往的特质,这是极其不容易的。然而,对于汉文化的深情并没有使陈开平沉醉于象牙塔里大唱赞歌,他清醒地觉察到珍贵的乡土人情在“外面世界”的冲击下正在渐渐蜕变,《云 叶子 麦地》于是乎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个人作品
父亲的季节
□陈开平
弃我去者,留我一世独殇。。。
这 样多早秋的午后,南风从父亲亲手种植过的葵园拂来,不时传来阵阵艾草的苦香,远处滚过慵倦的雷声,这样的季节拿什么奉献给您――世间的爱我者。
----题记
母亲上天捆起来挂在屋檐下的皂角,黑黑的皮,大大的角儿在空中摇晃。风,穿过皂角的黑皮发出“唰、唰、唰”地响声了,有两枚皂角是姐姐到树上用手擗下来的,带着几绺丝,细细地也在屋檐下飘。
父亲说,等再晒上几天,角儿干了,就可以掰烂一块洗衣服用。说这话的时候,父亲刚刚从社员会上批斗完不久,来到家,坐在祖父留下的碾盘边。他的腿有点发抖,裤管上还有被众人涂上去的泥巴,几根头发丢在衣衫上闪着蓝光。父亲望着皂角上飘飘的银丝儿,一动不动,身后是他亲手栽种的葵园,葵的头部都向西勾着,风抖动着葵头,天边不时滚过慵倦的雷声。父亲逢到这时就要说这种话的,唠唠叨叨,好象刚才批斗时落在他头上的柳条被雷声带过,放到天边、地崖似的,心头痴痴地举着凄艳的笑容,像倍受凌辱的妾。村的人说,他可能是疯了,不然总是说这些不天不地的话,谁能相信他不疯呢!
有一年春天,他起床很早,从外边归来就问我,听到夜里的萧音没有,他身上溢满了艾草的苦香,眼睛看着我,睁的很大,他的眼本身就很大,我那时还小,是他最小的孩子,只是很怕,我在被窝里点点头,眼睛望着他,他说,不知是谁吹的是《春江花月夜》,多美呀!我起了床,父亲拉着我的手到村西北的黄花地里,溜达一圈子,什么也没找到,风吹着我光秃秃的小脑袋。
我回到家,坐在门外的碾盘上。
父亲进了屋。
母亲在门外洗衣服。革委会主任走进来说,今天要批斗我父亲,母亲把手从盆里拿出来。说,他大叔,他爹这两天精神不好,是不是能过去这阵子呢?哪怕能晚上一、两天。曹主任说,这事已定好了,不要让他为难,父亲站在皂角树下象个楔子似的一动没动。一会儿把母亲洗衣服的水给泼出去了。
曾经几天,父亲穿过横七竖八的村弄,终于沿着一条斜斜的村路向外走去,他抓起一把马粪用鼻子闻了闻,他的脸皮向上提了提,又胡乱地抓一把麦苗塞进口袋里,拾一片碎瓦,那一枚黑黑的皂角象一把刀一样。他说,可以掰开洗衣服,很好洗的。那是上一年,我家树上的皂角,是有点苦香的,他老是带着它到外边去溜达,村里人怕父亲跑了,就派人远远地跟在后边,父亲没跑多远又回到家里。回来的人说,八成是留恋孩子吧!
村里人说,怕是过不去这个秋天了。
村里人还说,他年轻上时砍高粱,一天能砍三亩地,三个妇女在后边捆都捆不上,热了,打一桶冷水浇到头上,没事。日本鬼子让他带路,他不肯,就用香烧他的腋窝,烧得吱吱地响,后来他还是给偷跑了......
这家伙够硬的!
有一天,父亲是用平板车拉来的,说是父亲睡在批斗台上装死狗,父亲的眼直直地,身体有点发抖。母亲说,还在发烧,我在村后的小河边乱转,心里总想着他,母亲用毛巾勒在他的头上,上面敷上凉水。父亲说,他觉得头上在冒火,母亲半信半疑,父亲半夜就睡着了。
村里人的话是没法儿信的。那年秋天,父亲还在小葵园里除草。我的父亲宽如大坝的肩膀消瘦的如同木架,散发出皂角一样的气息,我说:爹,你不会死的,别人都说你过不了这个秋天了,是怎么回事呢?父亲看着我,大大的眼睛在空中闪着白光,我怎么知道呢?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只是好难过,我好想他,他的头上有物体敲击的疤痕,我感觉不到它们的不适,好象每一个都是应该嵌进去的,无它无以致远......
父亲平反了。父亲在小葵园锄草,南风拂来,葵头和父亲的头颅在不停相碰。一会儿,他抬起头说,以后呢?我听见了,我什么也没有想。父亲是初夏的一天跳到村后坑里淹死的。那是一天的寅时,父亲躲过母亲多天的盯梢,躲过老屋、躲过胡同里的那棵小槐树......为了事后让人知道,他把柱杖倚在坑边的一棵柳树上,一跳就死去了。发现他时身子直直地,在岸上只能看到他的头和头上的几块疤痕。那天,我刚从都市回到县城,正在和未婚妻吃瓜,是听外姓的四哥说的。
我和他做了二十六年的父子,就恩断缘尽了。
那 边
□陈开平
“梦也何曾到谢桥”。
―― 纳兰性德
一
如果时光可以追溯。
陈楼村前的土丘越来越松软了,地表皮掀起的块状泛起了白边,一块、一块像张荷叶,背阴的那边早期的藓苔由绿变黄继而再变成灰白色,随便捡起一块你瞧瞧,四周翘着,痴痴地举着灿烂、凄艳的笑容,中间较深的地方依然保持着伤痕累累年轻时期的温柔。
日子像秋天的树叶慢慢落下,收集成一方方的连绵丘状,被阵阵风儿吹过,重新调整了形态不知深浅的聚集起来,不规则地向前挨着。
二
春天,五福家打破的那个土缸有几块土红色瓦砾不知是谁又重新翻腾出来丢在了上边!土红色被一季的风雨打过早已经不是自己了,红晕得紧紧巴巴。。。。。。
高高低低的庄前院后苘林远视绿云。绿中泛黄,嫩黄的穗花夹杂在茎秆之颠咝咝低语,地上是一堆黄透了的叶子打着卷,绒绒的。
九月天,天空格外的青蓝,南风拂来,丝丝的柔软不可思议,白白的云层翻上跑下,像在空中迷失的马驹;有的厚如青山,不停地调节着丰富的形状,像山洞,像村庄、像羔羊、像树木、像学校,清淡相间,一丝一缕,细如蚕丝,在青空中飘荡。午后的太阳袭来,用鞭子随意甩一下把树叶缝隙中射下来的阳光划割地一段一段,稀里哗啦地作响,把太阳慢慢地逼下、逼下。接着蜻蜓们成群结队的从苘麻林、玉米地、高粱棵、野草丛中飞出来了,赤红的、火红的、红中带褐的、蓝色的、蓝中带黑条的、带黑圈的、全黑的。。。。。。相互奔忙着飞来飞去,五福和他的堂姐已准备好了用扫帚拍打。有人开始收工了,大大小小肩膀上和的篮子里发现:秋天将来了,庄子满了。
云层很厚,有的一层一层缠绕在一起,在村后河里遮遮掩掩、转转悠悠,忽而离开,忽而相聚。
陈楼的云是奈人的,有段时间,我沉侵在灵空的想象里,不愿意回家,那深厚而谈情有序的“房子里”一定隐藏着“青蛙四郎”和“那边”忘了回家的黑色毛驴 ,不然他们都会住哪里?
已经有多日不下雨了,天边好像还打过一阵阵雷声,渐行渐远似的:
“老天爷,别下啦,坑里蛤蟆长大啦”。
我的脸拼命的向上仰着,看着最远的那片云彩,它似乎还泛着红边,就干嚎起来,嗓子里涩涩的,眼里不时的走出了泪花。
“你怎么不让下雨呢!你没有看到那边在求雨吗?玉米都快旱死了。”姐姐梢儿说。
其实天气真的旱坏了,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落雨了,清晨看到那边的大叔在桂花家井口边穿上皂衣,头顶上带一个大大的草帽,两只眼圈描出了绿色,赤着脚,手里拿着两把木剑在井边转悠,身后带了桂花的娘还有几个男男女女,手里拿了锅盖、缸盖、大大的一块皂布等不同的物什,转了几圈就用手里的东西把井口盖上,然后口中含有不同的词汇,言毕,让一个最后边的年轻汉子突然把井口掀开,大伙同时把头伸到井边一声不响的观看。
姐姐说的是有道理的。
我没有什么“会说的”,看到天边泛红边的云彩,想到会做窝的蛤蟆我就说出了口,不知道它的所指,微风吹着我光秃秃的小脑袋,趁着梢儿不注意的当儿一转身向村后边的坑边跑去。
“。。。。。。坑里蛤蟆长大啦”。
我不敢大声嚎了,我在心中默默的念着,思索着头顶上带一个大大的草帽那边的大叔。他家与我家对门,说是对门也不是对门,因为中间相隔着被生产队充公的我家的三间房屋,前面有一个大铃,大铃就挂在我家同样被生产队充公的榆树上。我家的榆树什么时候被充公的我不知道,我知道那边大叔他经常到我家来告诉我的爹爹:什么时候批斗他!
他告诉我的爹爹:什么时候批斗他!大大的眼睛,一脸的无奈。他叫我的父亲为二哥,姐姐、哥哥们都怕他来,他似乎没有什么名字,我们家人都说:“那边”或者是“那边来人”了,大家心里就知道了什么事情了。
他常常地来,因为他通知批斗我父亲,我感到他与我们家亲近一些。
三
村后的坑边是坑的方向,也是我家的方向。
四
我家房屋的后面相传是一个后花园,我的一个远房的舅舅常常提起,他说的那个神色是我一生中再也没有见到任何人有过的神色,只要他喝点酒,眼睛就死死的盯着我们这些孩子,似乎还夹杂着眼泪,声情并茂的样子一直让人可怜,远房的舅舅说:当时我在我姐姐家“挂烟”,姐夫穿着白绢衫,剔着寸头,他像一个富有经验的士兵不停的指挥着,我的姐姐掂着被裹的小脚,穿着紫罗兰色的绣花鞋,她的一方雪白的手绢偶尔从袖口里露出来,亮亮的闪着蓝光,走起路来颤颤颠颠,我有时认为姐姐真美,没有任何人能与之相媲,她的美主要体现在走路上,我四叔就她孤苦伶仃一个女儿,从小对她要求及严格,听说姐姐六岁时就开始裹脚,一直到年老了她的脚与六岁时相差无几,下身弱,亭亭玉立,艰于步履若走路则窈窕,着力处全在臀部,秋天的天空很蓝,满满的河水从西边河口方向缓缓袭来直到流的没有尽头。河的对岸是一片延着河堤种的豌豆,红的、白的、紫色的花朵被早上的露珠打过。。。。。。烟叶就挂在后花园里,里面还有一课李子树,上面还有很多的蝉蜕,亮亮的。
我从来也没有见到那个后花园,我一直认为他那个厚厚的传说想必是他酒后懵懂之中的欺骗,那是他年岁已经六十多了吧,堂舅母不让其喝酒,他为了得到点酒来喝,故意使出的伎俩博得孩子们的同情。
我从来也没有见到那个后花园。
我见到了我家房屋的后面榆树条儿,密密地,有一人高了,西边是葛针栅栏,远处看浓密如绿云,一道道针状绿色的刺像外长着,头前褐色的尖。慌张的岁月匆匆而过,它像一支标枪依然遵循着原始的坚强和真诚,“后花园里”的故事早已不是黄雀之蝉。
还有那筒满满的河水,被隔的一段一段就绕在我家的房前。
坑里有水,坑里有鱼。
我家就在坑的南岸。
当它干旱至极,坑底没有水了,很快就长满了浓密的抓地央、布谷苗子。。。。。。坑的那边是一片芝麻地,里面不全是芝麻,还要一些蓖麻和葵花一类的作物,高高低低,日头浮在庄家上,风一动有荡Z阳光的声音传来,野高粱不远处一棵一棵的最为耀眼,被风一吹像个赤红的哨兵东张西望的摇晃着,阳光与各种颜色在稠密的调和着。【未完待续】
老人茶
□陈开平
老人茶,路伴能归家──游子吟远远地就能看到这个小茶馆了。它不靠个村子,离镇上也稍远,所挨着的只有一条宽土路和庄稼苗儿了,夏天里有四只小柱子支着,上面铺上油毡,再盖上青草柳树枝什么的,小柱子用绿色油漆得亮亮的……挨上秋,四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