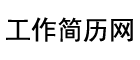陈芳允的个人简介
陈芳允(1916年4月3日―2000年4月29日),出生于浙江黄岩,中国无线电电子学家,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陈芳允长期从事无线电电子学及电子和空间系统工程的科学研究和开发工作。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获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
陈芳允著有《无线电电子学的新发展》《卫星测控手册》等,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1986年,他和部分院士联名建议发展中国的高技术,促成了中国发展高技术的“863计划”。
人物生平
1916年4月3日,陈芳允出生于浙江省黄岩县,父陈立新,毕业于保定军校,母许氏。
1921年,陈芳允开蒙,次年,生母病故。
1928年进入黄岩县立中学读初中,1931年到上海浦东中学读高中。
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在机械系,后转人物理系。
1938年初,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学习。物理系中有任之恭、孟昭英教无线电课,他对其中的实用无线电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在任之恭先生的建议和推荐下陈芳允先在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做无线电通信有关的课题,后到成都航空委员会无线电厂工作,去后不久因搞无线电定向仪有成绩,被提为研究股长。
1943年,在成都与沈淑敏女士结婚。
1945年初,到英国A. C. 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先在伦敦实验室做彩色电视接收机的线路工作,后转至曼撤斯特工厂雷达研究室,参加海用雷达的研制工作。
1948年5月,陈芳允回到上海,在中央研究院生理生化所任技正。
1950年3月,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合并,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在上海成立分院,陈芳允在生理生化研究所任技正,在此期间,陈芳允为神经生理学研究完成了一套电子仪器(包括电刺激器、直流放大器及显示设备等),这是国内在生物电子学方面研制的第一套设备。
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
1953年调北京,主持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1954年并入物理研究所,组建成电子研究室,陈芳允任该研究室主任。
1955年陈芳允晋升为研究员。
1956年,陈芳允参加国家12年长期科学规划制定工作,并参加了新电子所的筹备工作。
1957年,原苏联发射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陈芳允对卫星进行了无线电多卜勒频率测量,计算出了卫星的轨道参数。
1958年4月19日,日环食带经过海南岛南端,是最好的观测太阳射电辐射的机会,当时中苏组成联合观测队,陈芳允作为中方领队和天文学家王绶g及原苏联科技人员共赴海南得到完美的观测结果。回京后,陈芳允协助王绶g创立了射电天文研究工作。
1958年,他开始从事脉冲技术研究工作。提出并完成纳秒级窄脉冲采样示波器的研制,把采样示波器做成可以携带使用的仪器,在国际上是首创。1963年研制出国际领先的纳秒脉冲采样示波器。
1964年,他和研究室的技术人员为空军研制出机载抗干扰雷达,由电子部工厂制造,装备了大量的歼击机。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飞机上使用单脉冲体制的雷达。
空间技术 技术负责人 东方红1号
1967年调到国防科委第26基地,从事卫星地面测控网的研制和建设工作。
1970年,陈芳允研究了美国阿波罗登月飞船所用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后,他针对通信卫星的测控要求,设计了新的微波统一系统,后被国防科委和卫星总体负责人孙家栋采纳。两套统一测控系统研制成功,为中国通信卫星发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此项目与通信卫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陈芳允为主要获奖者之一。
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为院士)并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
1984年调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任常任委员。
1985年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一起提出了对中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1988年后为国防科工委顾问。
1991年被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
1992年,陈芳允提出地球环境观测小卫星星座的系统方案。
1993年12月15日与姜岩讨论给江泽民关于纳米技术的报告。
1997年4月7日至10日,陈芳允与杨嘉墀、王大珩、王淦昌三位院士以“863”计划的名义发表了《中国月球探测技术发展的建议》。
1999年,陈芳允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4月29日,84岁的陈芳允因运动神经元病中枢性呼吸衰竭去世。
2010年6月4日,一颗由中国科学家发现国际永久编号为10929号的小行星1998CF1,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通报》第43191号通知国际社会,正式命名为“陈芳允”星。
主要贡献
卫星控制陈芳允是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1957年,原苏联发 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他即对卫星进行了无线电多卜勒频率测量,并和天文台的同志一起,计算出了卫星的轨道参数,该方法成为以后中国发射人造卫星所采用的跟踪测轨的主要技术之一。
1965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正式启动。陈芳允担任了卫星测量总体技术负责人。当时,卫星测量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特别是对卫星的跟踪观测到底采用哪种手段和方案,中国还没有经验。为此,陈芳允带领技术人员深入研究,大胆实践,反复论证。陈芳允不仅主持了技术方案的设计,还参加了设备研制和测量台站的建设工作。经过他与其他技术人员实地考察,分别在新化、南宁、昆明、海南设立了四个多普勒测量站。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地面观测系统很快抓住目标,进行持续跟踪、测量与计算,及时预报了卫星飞经世界各地的时刻。由陈芳允主持完成的卫星测量方案非常有效,不仅圆满完成中国第一颗卫星测量任务,而且为中国卫星测控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随后,陈芳允参加了中国回收型遥感卫星测控系统方案的设计和制定工作。那时正值“文革”时期,陈芳允被下放到陕南一工厂进行“锻炼”、“改造”,他顶住压力,排除各种困难,潜心钻研,设计完成了遥感卫星的测控系统方案,为中国第一颗遥感卫星成功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0年,参加论证并提出了原子弹试验用的多道脉冲鉴别器的试制方案,三年后,与同事研制了出原子弹爆炸测试用的多道脉冲分析器,交原子弹试验场使用。
频率分配技术1977年,中国建造了“远望号”航天远洋测量船,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拥有航天测量船的国家。由于船上多种测量、通信设备,光天线就有54部,各种设备间电磁干扰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陈芳允利用频率分配的方法,解决测量船上众多设备之间的电磁兼容问题,使各种设备得以同时工作而互不干扰,成功地解决了“远望号”船电磁兼容这一重大技术难题,并在中国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中首次得到验证。
双星定位系统1983年,陈芳允和合作者提出利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进行定位导航的设想,这一系统称为“双星定位系统”。这个系统由两颗在经度上相差一定距离(角度)的同步定点卫星,一个运行控制主地面站和若干个地面用户站组成。主地面站发信号经过两颗同步定点卫星到用户站;用户站接收到主地面站发来的信号后,即作出回答,回答信号经过这两颗卫星返回到主地面站。主站―两颗卫星―用户站之间的信号往返,可以测定用户站的位置。然后,主地面站把用户站的位置信息经过卫星通知用户站。这就是定位过程。主地面站和用户站之间还可以互通简短的电报。
2000年10月随着2颗北斗导航实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拥有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了。是继美国第一个拥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苏联第二个拥有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NASS)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美国GPS系统历时16年,耗资120亿美元,由24颗卫星组网,而中国的北斗系统只由两颗卫星组成,在经济上更算,而且中国的北斗系统某些功能超过美国的GPS,北斗系统它同时具备定位与通讯功能,不需要其他通讯系统支持。
“863”计划发起人1986年3月,陈芳允与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一起提出了对中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研讨、论证,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拨款100亿元,选择生物、航天、信息、 激光、 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制定了中国高技术发展的“ 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七十年代70年代初期,陈芳允就开始了通信卫星测控系统的研究论证。如何使地面测控设备控制36000公里高空的卫星?陈芳允提出采用微波频段,多功能统一在一套设备上,同时实现跟踪测轨、遥测、遥控、数传。1984年4月,这个系统在中国发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中发挥了很高的效用,1985年这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作为中国回收型遥感卫星测控系统方案设计和制定工作的主要参加者,陈芳允为中国十几颗遥感卫星的成功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再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为了解决远洋航天测量船的电磁兼容问题,陈芳允和研究人员经过两年努力取得重要突破,使几十套电子设备在一艘船上工作自如,这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陈芳允提出并主持了“双星定位系统”的研制工作,并在1989年演示成功,在世界上第一次实现地面目标利用两颗卫星快速定位、通信和定时一体化。
陈芳允兼任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被聘任为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是中国电子学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和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为院士)并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1985年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1年被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2年陈芳允提出地球环境观测小卫星星座的系统方案。1993年12月15日与姜岩讨论给江泽民关于纳米技术的报告。1999年陈芳允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0年4月29日,84岁的陈芳允因运动神经元病中枢性呼吸衰竭去世。
求学道路
黄岩县立中学(黄岩中学)
1916年4月3日,陈芳允诞生于当时还是黄岩县的城北陈家大院,5岁时开蒙,家中请了一个老先生教陈芳允读《论语》、《孟子》。1928年秋,12岁的陈芳允进到黄岩县立中学,也就是现在的黄岩中学读初中,他的父亲曾对他说过: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希望你将来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要在社会上立自己的业绩。因为父亲陈立信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在杭州一支独立营中任上校营长,后对国家前途失望,辞去官职回到黄岩,这句话对陈芳允影响很大,他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之路了。在学校里,陈芳允是一个尊师好学的学生,当时他的国语、数学、英语等主要课程成绩优秀,从这时起,他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
在初三快毕业时,陈芳允在毕业纪念册上写了一篇题为《送秋》的小文章。这篇文章坦诚地谈出了他对人生的看法。他认为送秋不送秋无所谓,对一个人来说是秋还是春、夏、冬季都要努力,不能虚度。
上海浦东中学
1931年夏,15岁的陈芳允考进上海浦东中学高中部,进入高中没几天,就碰上了“九·一八”事变,陈芳允积极参加上海学生运动,抵制日货游行,上南京请愿,后请愿学生被蒋介石派兵押上火车送回上海。同样是“863”计划发起人之一王淦昌在1920年,也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
北京清华大学
1934年,18岁的陈芳允高中毕业,7月份大学考试即将开始,陈芳允报考了当时的上海交通大学与北京清华大学,由于两所大学试卷不一样(交大的试卷考题多,内容繁杂;清华试卷难度虽大,但题目少而且灵活,这样的题风刚好对陈芳允的学习路子),所以上海交大落榜,清华榜上有名。
考入清华的机械系,当时上的第一堂国文课就是由著名文学家朱自清讲授。陈芳允在机械系读一年后,对机械不感兴趣,却对物理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物理课上,每周小考一次的物理成绩他总是优秀,物理课的期终考试成绩他得了最佳,分数为S+。那个时期,清华大学的考试成绩采用5分制的计分办法,S表示佳,S+当然就是最佳了。有了这优异的成绩加上物理课对陈芳允的强大的吸引力,他下决心做出了转换专业的选择,后他转换专业进入物理系,投在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门下。吴有训在教学过程中,也已经注意到这个物理成绩优异、又心灵手巧的学生陈芳允。他虽然不大爱说话,但做起实验来有板有眼、井井有序。他发现这个学生的眼睛非常专注地观察他的实验,不放过任何一点细节,不仅一丝不苟地做记录,而且善于动脑子提出问题。吴教授打心眼里喜欢这样的学生,所以当陈芳允提出想转换专业的请求时,得到了吴有训的大力支持。当时,物理系在清华是很难进的,因为陈芳允的普通物理课学的好,吴企孙等任课老师都很赏识他,因此在转系时被物理系所接受。陈芳允把对恩师的感谢深深埋在了心底,不断激励自己努力学习。
留学英国
1944年,美国利用“租界法案”款项,英国由“英国工业协会”招考培养一批中国技术人员,到美国和英国的工业部门学习工作。陈芳允先报考美国的电影工程专业,后又考英国的无线电工程专业。先得知被美国录取,到重庆教育部报到,因被工厂阻挠,未能出国。在重庆又得知英国也发来了录取通知,由航空委员会机关直接介绍报到,到英国留学。在英国伦敦A.C.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从事研究彩色电视接收机线路改进工作。此时他业余到伦敦大学听课。在英国期间,他参加了英国第一套海洋雷达的研制和船上试验工作。
人物评价
陈芳允于197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认为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革命行动的指导,也是科技活动的指导。他说:“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使我恪守终身。……为科学求真理,为技术进步,为建设祖国,都是为人民服务。”他长期不懈努力拼搏在科技战线上,也正是这一信念的体现。他坚信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必可达到繁荣富强的境地,而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将迅速发展而立于世界之林。
“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四十年京兆一技人,求新服务不爱名,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赶超心!”这是陈芳允写的两首诗,也是他的人格和精神很好的写照。
卓越贡献
陈芳允,早期在国内领先研究毫微秒脉冲技术,领导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机载单脉冲雷达,为我国无线电电子学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99年的9月18日,人民大会堂召开表彰两弹一星功勋奖章(515克黄金铸成)获奖专家大会。会上,江泽民向23个对两弹一星有贡献的专家授予了功勋奖章,值得一提的是:23位中有14位功勋科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有11位科学家出自一个老师门下,――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其中有一位就是陈芳允。
陈芳允之所以能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与他对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作的贡献密不可分。
不朽精神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革命理想
陈芳允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科学家,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人生路必曲,仍需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
早在三十年代,陈芳允上中学时,就立志要用知识报效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主义运动。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肆意蹂躏,陈芳允感到莫大的屈辱,由此,他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 ”这个真理,从而更加坚定了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的理想抱负。
1948年5月,陈芳允从英国回国。在上海不愿为国民党打内战出力,拒绝航空委员会调派去上海机场工作,同妻儿回黄岩老家,受到工厂记大过处分。10月,正值淮海战役期间,航空委员会调陈芳允去南京工作,他不愿帮国民党政府打共产党,跑回湖州找当医生的岳父为他拔去一个脚趾甲,造成假伤,回到上海住进医院里。
上海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陈芳允参加维持秩序的革委会,劝阻中央研究院的科技人员不要跟国民党去台湾。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献身科学的精神
有人说:要记住陈芳允,只需记住他的两个特点就行:一是自己给自己理发,二是自己给自己缝补衣服。陈芳允的头发长了,从来不去理发店。他说,去理发店太费时间,不是理发师傅等你,就是你等理发师傅,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结果还未必满意。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练出了一手绝活儿――自己给自己理发。陈芳允的另一招是自己给自己缝补衣服。由于他的祖父是有名的裁缝,所以他从小便与针线打上了交道。就是在81岁高龄,一旦衣服烂了需要缝补,只凭一种感觉和经验,他仍能将手中细细的线轻松地穿进那个小小的针眼。
陈芳允对工作是高标准,对生活却是低标准。他病逝后,在他家里,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连褪了色的布窗帘也舍不得换。但他为我们国家所须所做的贡献却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从863计划的提出到2000年,十五年,“863”计划15年中获国内外专利2000多项,发表论文47000多篇,累计创造新增产值560多亿元,产生间接经济效益2000多亿元。
863计划突破的关键技术在与产业界的密切合作下,使我国在生物工程、药物、通信设备、高性能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平台、人工晶体、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等国际高技术竞争的热点领域,具有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这些产品开始形成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实力,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生长点和源头。
情系母校、关心学子的情怀
作为黄中毕业的校友,陈芳允对黄岩中学怀有特殊的感情,对黄岩中学的发展非常关心,1995年6月5日,陈芳允为黄岩中学题词:愿黄岩中学发展、提高,为家乡及全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材。
在1999年住院期间,陈芳允以《漫漫人生路拳拳报国心》为题,给他少年时黄岩中学的同学王克晟(黄岩中学的老师现已退休,也是王有器老师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思想观念的发展历程,以及自己工作的情况,并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对母校的学生起鼓舞作用。这封信后来在黄岩中学2000年1月的校报《清献园》上全文登载出来。此时的陈芳允已经病的很重,但他还特意托人给他的母校黄岩中学随信寄来2000元钱,表示支持母校建设的一点心意。这是陈芳允一生中写的最后一封长信。
陈芳允对黄中的学子怀有殷切希望,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我们的同学:人生道路的选择,思想观念的发展起着根本的作用。
主要论著
1《无线电电子学的新发展》科普出版社,1963(1979年内蒙古出版社再版)。
2《计量测试技术在空间测控系统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宇航学会计量测试年会上的报告,1981。
3《空间统一测控系统设计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电子学报,1985。
4《全数字通信技术》中国通信学会特刊:新的技术革命与中国通信,1984:4~10。
5《太平洋地区国家卫星发射与测控技术发展与合作的前景》(英文),国际宇航联学术会议上的报告,1986。
6《发展我国的星基定位通信系统》中国空间科学技术,1987。
7《我国航天技术发展与技术科学》中国科学院院刊,1986。
8《中国航天测控网及其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英文),国际宇航联学术会议上的报告,1988。
9《关于建设我国灾害测报监控系统的建议》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灾害防治讨论会上的报告,1990。
10《卫星测控手册》科学出版社
文章转载
卫星上天,我们测控
作者:陈芳允
“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
我在1952年受中国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嘱托,开始筹建电子学研究所。1953年秋天,钱三强从苏联回来,他为研究原子能办起近代物理所(后改称原子能所)。钱三强知道原子物理研究工作离不开电子学,例如加速器、射线测试等都要有电子学知识的人来做,提出要我们到他们所去一起干。我则认为电子所筹备近一年,已具备一定的人员和仪器规模,停止了筹备工作可惜。
那是195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吴副院长把钱三强和我找到他家,进行协商,直到深夜。钱三强反复强调电子学对核物理的重要性。经过吴副院长的协调,最后我们达成一致:电子所筹备处先并到原子能所作为其一个研究室,由我带着一部分人配合物理方面的研究,为原子能所做工作,其他人仍继续做电子学发展几个重要方向的工作,继续筹备电子所,我们这些人不散,到一定时候再全部撤出来建科学院电子所。这样,在1953年年底,我们并入了原子能所。
1956年,在十二年科学规划后,中国科学院实施“四项紧急措施”,组建电子所、半导体所、计算所和自动化所。钱三强信守诺言,同意我们从原子能所撤出来,他仅仅留下了两个人。钱三强是一个很值得人们佩服的人,我们都很尊敬他。
顾德欢、马大猷、孟昭英和我是电子所筹备组成员。电子所成立后,我任四室主任,主要搞电子线路的研究,对和核物理有关的电子仪器的线路研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1962年,由于核弹研究的需要,要求我们做了一台多道脉冲检测仪,这个仪器是用来测量射线的。如果说,我们为“两弹”做了什么贡献的话,也就这么一点儿。
我在中科院电子所四室任室主任时,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大约是1963年前后,我们做毫微秒脉冲的产生、放大和观测,做出了一台毫微秒脉冲取样示波器,是国际上最先做成功的,参加了国际展览;接下来,我们做多道脉冲检测仪;1964年,我们开始改进机载雷达,这种雷达后来在电子部投入批量生产。
卫星上天我们测控
1957年是国际地球物理年,科学院赵九章先生很早就提出能否放卫星。后来苏联放了。
我是搞电子的,对卫星发的无线电信号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苏联放卫星后,我和张志诚,还有研究室的其他几位同志,合计着能否收到苏联卫星上的无线电信号。我们开设了一个小小的课题(并非上面下达的任务),几个人一起做了一台接收无线电信号的装置。后来,搞天文的同志也加入进来了。
苏联的第一颗卫星早晨太阳没出来时能用肉眼看到,我起来看到过2次。我们接收到它向地面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及频率变化(称为多普勒频率),并计算出它的轨道,还推测了一下它里面可能有些什么内容。
1965年,赵九章、钱学森向中央提出搞人造地球卫星。在毛主席讲了“我们也要人造卫星”以后,科学院正式组织研制卫星,称为“651”工程。在此之前,科学院已经组织实施“581”任务,研制了探空火箭,他们就成为“651”的基础。在对卫星的跟踪测量方面,则于1966年组织成立了“701”工程处。当时,这项工作有天文、电子、光学等三方面的人参加。
赵九章先生在清华做过助教,我在清华物理系读书时,他辅导过我们的实验工作。大约在1966年的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出家门散步,迎面碰到赵九章先生和其他几个人,他对我说,“我们搞卫星,无线电非常重要,这是重要的一环,卫星发出去后就看你们的了”。
我在“701”工程处工作后不久,便被部队(国防科委)的基地接管了。领导先叫我到天桥无线电厂劳动了近一年,就到陕西某地工作。因为搞设备和设站,四处奔跑,以后就再没有看见赵先生。没想到后来赵先生竟被“造反派”批斗致死,这是我这一生想起来就很难过的事。“文革”时期,我虽因为到了部队,没受到冲击,但是心里对为什么要这样搞实在想不通,家里也曾被红卫兵抄过一次。当时我倒是把毛主席著作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但是也找不到答案。
人生断想 偶然际遇
我的经历,想起来有许多偶然的际遇。
1938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总想为抗战做点事,就到了航空委员会的成都无线电厂,做飞机上的导航设备。有一次,国民党引进了美国的导航台,在重庆,让我去装。装好后,他们让我把导航的方向指向西安,我感觉不对头,因为日本人不在西边,于是产生了离开那个工厂的想法。
在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美国、英国在中国招收一批人员,预备战后在中国做生意。我就是想离开工厂,先后报考了美国的电影工程和英国的无线电技术。1944年夏秋之交,先通知考取的是美国的电影工程。通知我到重庆教育部报到出国。我到了重庆,教育部说厂里来信不放我走。我就去找好友陶晓光,他是陶行知先生的儿子,我知道陶先生和解放区有联系,有可能想办法到解放区去或是找件别的事,就不回成都了。记得当晚我在他家一直等到深夜,陶晓光都没有回来。第二天,我在街上徘徊,恰好碰到了航空委员会一个干部,他告诉我,说我已经考上了英国的无线电技术。因此,我就在重庆报了到。回到了成都,厂里也没有说什么。于1944年底出了国。?
在英国,我在一个工厂的研究室做过海用雷达的工作,1948年回国。到上海后,国民党希望我去飞机场工作,我不愿去,他们又让我去南京,正是淮海战役的时候,我坚决不帮国民党打共产党,想出了一个不去的办法。我岳父是名医生,我就让他把我左脚的大指甲盖给拔了,因此就住院了。后来,从成都搬回的无线电厂(后改为一研究室)的厂长,干脆让我住进了正规医院。1948年底,我到了冯德培先生(在英国时认识)的生理生化研究所,做神经电脉冲的测量设备。
我的一生中,回想起来,遇到的偶然性事件相当多,有些可能会影响到一生的工作和生活。但是从中学开始逐渐地从对国事的了解,学生运动的参与和体会,革命队伍中熏陶,逐渐地立下了志愿,跟着共产党走,为祖国和民族的振兴而工作和贡献一切,则是一成不变的了。如果说在工作中有一点成就,也正是从立志而来。
测控方法有些争论
部队接管“701”工程处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非军非民,经常穿一套蓝色衣服,战士们叫我“老师傅”,这倒让我觉得很合适。我真正参军是在1975年,已经快60岁了。
对于卫星的测控,许多工作都是和大家一起做的。只是在一些方案、思路上提得多一点。对第一颗卫星来说,在测量方面,卫星发射上天后,有3点最为重要。
第一,卫星是否已经进入了运行的轨道?
第二,卫星的轨道是什么样的,是否符合预定的要求?
第三,卫星运行中,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点上空的预报。
1965年年末,科学院开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讨论卫星的研制和测控问题,会上有些争论。在测量方面,光学观测是需要的,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考虑到天气不好时光学看不到,还得有无线电测量。争论的正是无线电测量方法,特别是对入轨点的测量,当时,苏联和美国主要是采用干涉仪。天文台的一些同志坚持要用干涉仪,电子部提议用雷达,我主张用无线电多普勒测量。最后的意见是在入轨点,光学、雷达、多普勒都用,可以说是为了保险,干涉仪则在入轨后的第一个观测站和第二圈经过我国上空时设置拦截观测,但是是试验性质。
关于如何设置观测站的问题,我们国家不像苏联经度跨度那么大,受地域影响,我们一定要适当选择站址,才不会“丢”了卫星。我们考虑卫星上天后的第二圈在新疆那边看,十多圈之后,则转回到东部沿海可以看到。这样,在新疆西部的喀什、东北和胶东地区设观测站就非常重要;此外还考虑了其他一些地方,因此,先后建起8个站和一个测控中心。后因发射静止通信卫星,又增加3个站和测量船。
在卫星测控中,我思想上有几项原则。第一,设备要有高的效率,但是也要尽量地简化,从国家的经济和人员的情况看,尽可能快地建设自己的测控网。提出的新方法更要考虑是否比旧的方法效率更高,效费比更高。第二,结合中国的条件考虑,我们要求仪器效果不低于人家,但是要想法以中国的条件来达到。当然,如果有些新的元部件,我们也可以自己做。我头脑中一直有一个念头,既然我也学了这些知识,我们应该有自信心,只要干,就不会比人差。
卫星观测一共包括四个方面,其中三个是测控,叫做TT & C,即跟踪、遥测和控制,还有就是通信。通信把各个系统、各个台站和中心联结到一起。
当时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是:“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我们做到了。我做的是偏重于测控设备方面的工作,实际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软件工作,如测量到后,计算卫星轨道,管理卫星的运行和控制执行某种任务等,也都需要在TT & C中做。??
测控技术与观测站点
对我国放第一颗卫星来说,“抓得住”是卫星测控中最主要的一道难题。如果卫星送上去了,自己却没有看见,不知道卫星到哪里去了,也不好宣布发射成功了,因此大家都很关注。
“抓得住”最主要的是对卫星入轨点的测量。当时估计我国第一颗卫星的入轨点在湖南南部到广西北部一带,因此在这一带设观测站是必要的。但是用什么测量设备呢?光学设备是肯定要用的,光学经纬仪可以起较大作用,但在当时也让人感觉不放心,主要是怕天气不好时看不见。因此,在关键的闽西站,光学、雷达和多普勒三种方法都用上了,在南宁还使用了干涉仪。由于多普勒实时定轨需要多站观测,因此,在闽西、南宁、昆明和莱阳都装上了多普勒,根据多普勒数据可以定出卫星运行的轨道。雷达主要是用来测量距离和卫星角度的,跟踪卫星上的应答机,测量一段距离后,可以算出卫星轨道。
观测站点的选择,主要是和天文台的同志一起商量。因为还有卫星入轨后的第2圈,将经过中国西部边界附近的上空,大家认为这一次的观测也很重要。因为这次测到就可以完全肯定卫星运行正常,同时,测量以后可以把轨道算得更加准确。因此,一致的意见是在新疆西部喀什设站,并安装光学、多普勒和干涉仪等设备。卫星经过十多圈后,回到我国东部沿海上空,这时就要靠东北和山东的站了。卫星的测控中心设在西安,管理和指挥各站工作。各站测得的数据,经过通信线路送至中心,中心计算机综合各站数据,计算出卫星的轨道参数。需要卫星做某种动作时,中心发出遥控指令,经过适当的测控站发往卫星。
在研制第一颗卫星时,地面系统考虑观测较多,没有控制。东方红1号一上去就自动唱起了东方红,没进行遥控。
东方红1号卫星在发射时,我们正出差在科学院上海科仪厂,讨论新的测量设备。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走在街上,听到新闻公报,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并传来了《东方红》的乐曲声。这说明我们的测控系统也成功了,真的很激动,很高兴。
统一测控系统
7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有人提议搞载人飞船,我自然想到将来的测控问题。我研究了美国登月球时的测控方法,他们用的是微波统一测控系统。后来我们的飞船项目暂时不上了,但是我想为什么不把统一测控系统用在别的项目上面呢?例如通信卫星。我和几个同事就给通信卫星设计了一套统一测控系统,当然与美国的不一样,用了一些新方法,上报给上级部门。当时有很多人觉得没必要,那时的测量、遥测和遥控都是分开搞的,各成体系,各自归不同的单位管理,如果搞统一系统,怎么能合在一起呢?结果,发射中心参谋长支持这个方案。方案报送到国防科委后,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赞成,通信卫星的总设计师也赞成这一方案。原因是用了统一系统,就可以将卫星上各种测控信号都调制在同一个载波频率上和地面联系,这样卫星上就可以省去好些设备,特别是天线,原来需要几套,一套就够了,对卫星十分有利。
这个方案得到批准后,到底谁来做,又发生了争论。最后的结果是四机部做一套,七机部做一套,国防科委科技部的同志和我在中间做协调工作。
远望号测量船
观测卫星在海面上空的情况只能依靠测控船,特别是发射静止通信卫星。卫星不能一次就定点在36000千米高度某一经度的赤道上空,需要控制它进行两次变轨,测控船起关键性作用。早在第一颗卫星发射之前,国防科委基地的技术人员就提出需要测控船(因为导弹试验也需要)。我们的两条测量船,远望1号和2号是在文革期间造的,我们在船上装了对卫星的测控设备。在发射静止通信卫星之前,还装上了统一测控系统设备。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测控船。?
发射静止卫星的过程是先把卫星送到有一定倾角的400千米或200千米高度的椭圆轨道,当它经过赤道时要进行变轨,要变到36000千米高度的圆轨道,还要把轨道倾角转变为零。这些测量控制需要在海上进行,靠船上的测控设备来完成。船上还有大功率的远距离通信机,与国内的测控中心联系和传递测量数据。因此,船上的设备多,无线电天线也多,发生了电磁互相干扰的问题;特别是大功率通信机一开机就会使好些设备受到干扰而不能正常工作。当时的一个办法是先把信号用小功率送到几十千米以外的另一条船上,再通过该船上的大功率发射机将信号发回国内。即使这样做,仍不能解决全部干扰问题。?
为了保证发射静止通信卫星时测控船所有设备都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国防科委的测量通信总体研究所和远望号测量船上的技术人员,我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把“文革”时期搞的不严格的工程加以改正和完善,另一方面提出了一套频率分配的算法,使各种设备选择使用的频率避开其它设备的频率,包括可能产生的一定次数的谐波和组合波,这样就避免了互相干扰。测通所计算室的同志做了大量的计算工作,我们又在船上做了海上试验,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就此解决了电磁干扰问题。测控船后来在发射通信卫星和远程导弹中起了很大作用。??
对“两弹一星”精神的体会
对于一项大的系统工程,从科研到开发到实用,我觉得没有比大力协同来做更重要了。放卫星的工作,包括卫星本体、发射卫星和对卫星的测控三个方面,每一方面都需要多个学科和多种技术的协同工作才能做成。就拿测控来说,我在前面提到的主要是关于测控设备和建立观测站等问题(因为自己的工作在这一方面),但是还有重要的方面是如何计算卫星的轨道,如何控制卫星的运动等工作,如果没有天文和计算数学的人参加,则有了设备也没有用。进一步的创新工作更需要多个学科,从基础到技术的人都参加。我自己在许多问题上常感数理基础不够,也深感要没有大家的合作,就不会做出一些成绩。在几十年的工作过程中,我还感到中国人的刻苦耐劳,为民族、为国家的精神在世界上是无可比拟,远胜于人的。记得在我们为建立测控站而四处奔走时,也正是“文革”十分紧张之时,火车上拥挤不堪,我和青年同志们一起,有时站着也谈工作,吃不上饭、睡不上觉,但工作还是做好了。因此,我相信,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无论是国防事业,还是民用设施,如果再有与“两弹一星”类似的大项目,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大力协同精神,我们一定能超越他人,圆满完成。
对于个人,我在“一二九”运动时,只是民族先锋队的外围人物,受到同学的启发对共产党有所了解。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和思考,逐渐树立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的信心和决心。解放前夕我从国外回国,就想方设法不为国民党效力。全中国解放以后,正是我的壮年时期,自然力求以所学的专业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学用结合,边学边用,为祖国的现代化而努力工作是我的志愿。在“两弹一星”中,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学校搬迁,自己又生过几次病,学习基础不够,影响到许多工作做得不够好,心中还有遗憾。“文革”期间我到了国防科委,没有受到冲击,只是开始时被下放到无线电厂劳动了一年,与工人同志关系相处非常融洽,并帮助他们解决了通信机生产等类似一些技术性问题。不像许多学校里的老师和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受批判,没有工作做,去扫厕所。我没有丧失这五六年为国家工作的机会,感到很是幸运,并且十分感谢部队的信任和支持!
希望科学院起更大作用
“两弹一星”,科学院起了很大作用,希望科学院在今后的国民经济建设中起更大作用。科学院各个学科都有,有利于各学科的融合与交流。科学院有良好的基础研究传统,可以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建立提供后盾。
对于创新,无论是基础性研究抑或高技术研究,学科之间、基础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了解、交流、交叉和协作是十分必要的,他们的相互融合也会互相促进各自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中科院学科齐全,基本囊括了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这使得各个学科交流十分方便、快捷。当今科技的发展与创新,如果没有学科之间的交流,很难有所创新。举例来说,准备研制的对地观测小卫星系统,就是我们和地学部的陈述彭院士等人一起提出的,这是典型的空间技术与地学的结合。
其次,中科院有很好的基础研究传统。如纳米技术的研究,对电子学意义重大,将可能使“微电子变成纳电子”;原子钟不仅是计时最准确的钟,还是计量的基准;高温超导材料的使用,可以使卫星上许多零部件体积缩小;许多基础性研究,中科院已经进行到一定程度,只要再往前走一步或两步,并互相结合,对工业部门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国家很重视高技术的发展,这不能没有基础性研究。高技术需要基础研究,同时反过来也促进基础研究。我们的科研现状,在协作方面表现出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科研上的有些事情,互不通气,不了解,这很不利于发展与创新。
我们希望科学院能像在“两弹一星”的工作中那样,能和其他部门大力协作,更多地解决国家经济发展中急需的问题,同时,看到未来的发展,以创新的研究成果作为产业部门的先导和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