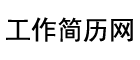程士庆的个人简介
程士庆,祖籍衢州,生于上海。中共党员。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2001年又毕业于浙江大学新闻系。1989年起在浙江省文联工作至今,现任《少年儿童故事报》社长、主编,副编审。基本内容
程士庆简介:祖籍衢州,生于上海。中共党员。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2001年又毕业于浙江大学新闻系。1989年起在浙江省文联工作至今,现任《少年儿童故事报》社长、主编,副编审。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全国文学艺术性少儿报刊专业委员会主任,浙江省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省记协、报协理事。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集《大学一年级――二十岁的坦白》,出版(含主编)文学作品8部。2004年获第七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论文遴选奖。
相关作品:
《二十岁的坦白》
很久,没有这样的心境了。
当二十根红红的蜡烛即将燃尽的时候,我点燃了一支自己平生第一支香烟(我没有成为一个烟鬼,像大学里很多人那样,仅仅因为我很爱惜自己)。
二十岁了,经常会这样莫名其妙地感到寂寞,感到烦闷,甚至感到没有了自己。
于是,便会经常喜欢一个人在一个朦胧的雨天,呆呆地阅读雨滴在玻璃窗上写下的湿漉漉的文字,默默地开始守护起一个也许是刚刚诞生的秘密,体会到一种涩涩的不是滋味的滋味。
似乎有很多事情一下子拥到面前,可你来不及分辨,来不及捕捉,一切便又悄然远逝。
只是,此时此刻,就在眼前这袅袅升腾的烟雾中,一切却好像一下子明朗了许多。
二十岁,一切都已无可挽回地改变。
只记得昨天还是一个懵里懵懂只知道五分钱能买一根冰棍的孩子,今天却已经学会不很老练但很坚定地搬弄着刚从这里或那里得来的现货,数落着这位或那位老人(不只是年龄)的不是,虽然更多的时候还是为自己和这个世界感到这样或那样的困惑。
也许,这真是一种世纪的悲哀,很多人都在叫嚷着活着没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想去死。谁都想活,还要活得有滋有味,于是便只能习惯去干一件事后想来肯定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以感到生活得很有意义,习惯用一种夸张的近乎癫狂的热情去迎合世人的眼光,来掩饰自己内心消极的真实。只不过,会在某个快乐的节日里,在有着最丰富的色彩可供陶醉的时刻,却只想面对着除了没有还是没有的墙壁,为又一次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生活得很苦而平静得想哭。
我知道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中的一个。
我也知道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在这样一个有着临界意义的年龄,会一下子发现自己的生活有着那么多缺憾。实际上。只要想想自己这二十年的生活轨迹为什么只能是这样、而不能是那般,你就会突然心里空落落的,为自己哪怕是再顺利的生活。因为,未知总是充满诱惑的美丽。
当然,严格地说,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缺憾,毕竟任何道路的选择都只能意味着选择其他道路的不再可能,可即使是明白了这一点,很多人(譬如说我)还是无可奈何的感到不无悲哀。
不过,说来或许不被相信,这个年龄的我们喜欢的就是自寻烦恼。
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有时明明意识到自己在做了某件事情后会后悔终生,甚至有时明明知道怎样会有一种相反的结果,可是他仍然固执地走向悲剧,走向悔恨。
我就这样做了,没有什么别的原因,仅仅因为我很自卑。我要以失去自己最不能失去的来证明我还行,我还能战胜一切。
真的,多少次梦中惊醒,坐起身看看四壁,望望窗外静寂的世界,我都是心里害怕得要命,觉得此时此刻哪怕是世界上最弱小的生灵都能毫不费力地吞噬自己。每次我都是赶紧把眼闭上,为又一次发现自己灵魂深处的怯弱而惊惧不已。
我不能容忍自己的软弱,而消除软弱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学会残忍。在我终于明白自己将不得不作出某种抉择之后,我心里真是痛苦极了,我比谁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这样做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最需要慰藉的时候却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在最需要温暖的时候却只能望着别人散发着笑声的窗口发呆――可最终我还是以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冷酷,重重地推开了那已被证实的微笑,并很兴奋地品味到一种自己渴望已久的悲壮。
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我认命了,我不能怀疑自己的抉择是否就真的那么明智。我相信我还会大笑的,因为我大哭过,我还会大喜的,因为我有过大悲,仅此而已。
我做过许多梦(谁又能没有呢?在二十岁这本应还是多梦的年龄)。
我一直期待着自己能拥有一种震撼自己整个身心的爱,对一个我所第一眼便认准“就是她”的女孩。
遗憾的是,我是遇到了,却只能瞩望她的背影,虽然我们已经走得很近很近。
感情的事说不清楚,她这样告诉我,我也同意(能说清楚的还叫感情吗?)
我不会纠缠谁的,除了我自己。而且,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终于心平气和地发现自己现在实在也经不起爱,这当然包括爱人和被人爱。
爱人固然苦恼,被人爱也并不轻松。我还太年轻,还不能肯定什么,也无法保证什么,这就是一切。
我很喜欢这样一首歌:寂寞的小男孩,他从街上慢慢走过……我觉得那唱得正是我。总是喜欢在一个蒙蒙的雨天,漫无目的的走上大街,流浪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又总是忘了带伞,于是便总是期待着远方会有一个女孩,撑着花雨伞向着我迎面走来,可每次结果却总是不妙,不等她走近,我已经被雨打得湿透……
尽管如此,我也并不认为这二十年中有过挫折,我更愿意把我生活中那种可以称之为挫折的遭遇看成是一种经历,一种能极大地丰富和延长我短暂人生的经历。
即使有过这样的时候;在我感情最难煎熬期间的一个夜晚,我和她正好在路上碰见,彼此还是以一种别人根本觉察不出什么异样的平淡口吻随便聊了几句没放一点味精的话(一直想有点涵养却一直没有的我此时才算有了那么一点涵养,其实只要会装就行)。告辞以后,望着她在夜色中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突然特别的难过,实在难以排遣,就独自一人跑了出去。也不知自己要干什么地一直到了离校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气温很低,还下着雨,开阔的广场上一个人影也没有,连平时应该是最耐寒的情侣也没见着。我衣服很单,人冻得直打哆嗦,可还是鬼使神差地往上走,到了纪念碑下,我伸出手掌,重重地拍打着碑石,手心一阵发麻的疼痛,却使我感到一阵惬意的快感。听着这在寂夜里显得格外清晰的啪啪声,我一下子感到自己好弱好弱……
就在那天夜里,我无力地依着碑石,为自己流下了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的泪水。我不羞愧,而且,还为自己能具有这样一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具有的体验而欣慰得心尖发痛。
我更从来没有想到要忘记什么,这也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因为,你想忘记,只能说明你还在想。这大概是我在哪本书上看见过的,我想那位作家一定真正经历过一些什么,我是说真正。
相反,有时我真想说声:谢谢。也许,我真正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心境,一种失却部分人生后也就逼得自己无法对其它部分松懈的沉重。
我这样设想自己的未来:在一个远离尘嚣的海湾,我能拥有一座只要能抵挡住海风的小屋,里面只要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凳子,以及在我写累了到海边散步时,能拾到有人从海的那边寄给我的飘瓶,里面盛着只要能使我不致饿死的食物。等到我感到自己太老的时候(我指的不仅仅是生理),我便悄悄的来到黄昏的海滩,默默地将自己在这里写下的文字装进飘瓶,寄给远方的不知哪一个朋友(只不会是她,这没有必要,她应该有心安理得的幸福)。然后,我就轻轻的躺下,静静地等待晚来的潮汐将我带走,不留一丝痕迹……
事情就是这样,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却很简单。
当然,我应该是最没有理由感到孤独的,因为我有着比一般人多得多朋友,他(她)都是很好的人,我知道。
经常会受到远方相识或不相识的他(她)寄来的淡蓝色的信笺,为我那些写出之后便总是惶惶(不止是谦虚)的文字。
我却很少去信,即使难得有时想起来实在不好意思了,也总是不会超过“你好”几倍的寥寥几笔,可我确实是在经常惦念着他们,以我的感激。
我很难忘记曾有一次我是怎样真切的感受到友情的珍贵。那还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踢球时却摔折了手,当时痛得我只顾“哎哟”,老师和同学们闻声赶忙把我送到医院。等我稍稍回过劲来的时候,这才发现几乎班上所有的男生都来了,还有几个平实见我就翻白眼的女同胞。我不禁心头一阵发热,想说些什么表示谢意,可说出的却是一句近似玩笑的话:“托大家的福,还好不是右手。”大家都笑了,可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幽默。
毕业以后几年了,我已很少见到他们,偶尔碰上了,聊上几句便是长久的沉默――并不是没有话说呀,只是我们彼此都想着难得聚在一起应该多说些有意思的话而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或者有时干脆就只想大家静静地坐一会儿,什么也不用说却又什么都说了。
就在今天,当我读着朋友们为我的生日从远方捎来的祝福,我想了很多却都化成一句:我将努力,以不负他(她)殷切的目语。
我从来不写日记,不愿不能更是不敢。
有时,就这样眼睁睁地听凭许多思想飞快地走过,真是感到可悲可叹可就是不肯动笔。没有什么比担心被人耻笑更能成为理由的了,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跟别的任何人相比都是坏的可以。
不会有人想到,能在这里说出这一大串还算正经话的我也能在宿舍的夜晚,呼吸着不是脚臭就是狐臭的新鲜(应作“罕见”讲)空气,谈起女人这个永恒的话题也是眉飞色舞,并一举压倒群小的成为活得都已发黄的康熙辞典。
人往往不是他表现出来的样子,我同意这话,但又觉得似乎确切点应该是:人不可能同时表现出他的全部。所以上当受骗在所难免,并且只能怪你自己。
我太清楚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了,于是只好搁笔(原来偷懒有时并不是生性所致)。
我得承认,我伤害过人,有意无意地,不止一个但也不是很多。
我欠了很多情,我也深知自己带给别人的是怎样的一种创伤――会愈合的,但要留下疤痕,就像消愁的酒瓶碎在地上,留下的将是不会消失的印记。
我又能说些什么来为自己辩解呢?一个女孩子的第一次啊!
我可以不接受,到要珍惜!
我有拒绝的权利,但不应是满足虚荣的周旋。
我忏悔过,尤其在我终于明晓自己将因此而失去被我真正爱的信任后,我更是深恨自己。
我真愿自己能重新开始。但时光不能倒流,这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只能寄希望于时间了,我想我一定得证明点什么,否则到头来我真是一无所有。
我更愿你――我不说你出的名字,你能理解――你睡梦的夜空依然星光灿烂。
请原谅我,好吗?我知道我不配。
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读者,那么肯定已经不无诧异地发现我在这里写到的几乎都是女孩子,也早就有人为此嬉笑怒骂地对我旁敲侧击了。
其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告诉你,我喜欢女孩子,就像女孩子喜欢男孩子一样,并且我还相信,如果说与同性的放肆谈笑是一种愉快,那么与异性的相对无言更是一种享受。你要没这种感觉,不如趁早上医院或者干脆进宫。
我并不是柏拉图,但也没有成为登徒子。同样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正是因为我很有理智,正象一个……(不用说了,又是女孩子)对我说的:你的理智埋藏得很深,看上去很容易冲动,其实关键时刻却很能把握住自己。
我可不想在这方面弄出点什么事来,为这跌了跟头我会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这种事都是过眼烟云,我可是要干的事挺多。
我很看不起贾宝玉,但很欣赏他的一句话(也许专利权应属曹雪芹):男儿是泥做的,女儿是水做的。有时,我真觉得作为男人的心实在是太混浊、太干燥了,很需要女性的泪水来澄清和滋润。
我就是太需要了。每当我跟一个我所愿意深谈的女孩子深谈以后,我整个人都是异常兴奋,脑细胞活跃得我用笔都捕捉不住。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这样说,我的文章都是为女孩子而写的。
风流(如果这也算得上的话)而不下流,我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至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不要以为我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很多时候都是太不切实际了,甚至到了有点可笑的地步。
你能相信,一个男孩子被一个女孩子挫伤后,也许尽快另找一个是一种恢复心理平衡的最好办法,我周围就有人这样做,可我没有。我想我以后也不会这样去做。我想到的只是等待,等待着将来如果有一天我所挚爱的那个女孩子找到了她理想的归宿,我就转身默默地走开,一心去干我所唯一能寄托自己的事业。当然,如果正相反,有一天我远远地看到她走累了快要倒下,我就会走过去,扶住她轻声说:路正长,让我们一起走吧。
要知道,我现在说这话是当真而且需要勇气的。如果说最初表白时不是出于冲动,便是为了暂求一逞的甜言蜜语,那么,现在则是在我头脑相当清醒的时候,在理性的控制下得出的不被理性所左右的自白(不是表白)。我很清楚,这种等待对我来说也许终将意味着一种漫长到终生的流放,可我愿意,如果一种真正的感情终被证明在我心中真实地存在过,我也就死而无憾。
别不信,我会这样做的。爱就应该是不顾一切,对此我深信不疑。
这就是我的理想主义,即使最终碰得头破血流,我也不悔。
也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十分坦白的人,虽然我坦白了这么多。
我肯定回避了什么,但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实际上这样写而不那样写,与写这些而不写那些相去并不遥远。
很有可能,我是以最小的坦白掩盖了最大的虚伪,但我不可能说得更多了。况且,即使我说得再多,到头来也会被认作是以最大的坦白来为最小的虚伪开脱。
其实,我想再说的已有人代我说了:凡是我在这里没有说的,都是我不想说的了;凡是我在这里没有解释的,都是我没有必要解释的了。我愿至今还不理解我的人都不要再去理解了,我愿已经理解我的人都不要再对我说什么了,都沉默吧。
是的,什么都不用说了,还是沉默最好。
一根香烟是会很快燃尽的,我却丝毫没有察觉,直到红红的烟头灼痛了我的手。
也许,终将淡忘不了的,就是这样一个夜晚,这样一种心境。我想到了这样一些人和事――二十年的岁月啊!
二十岁不是忘却,我还会幸福地哭泣着,为一切都不会过去的记忆。
二十岁不是缠绵,我更会忧伤地微笑着,为一切都会到来的明天。
会的,我想一定会是这样的,请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