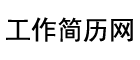初能变的个人简介
初能变,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
人物履历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能变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初能变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初能变、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初能变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o,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初能变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初能变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初能变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初能变的父亲初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初能变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初能变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初能变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跌骨折,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初能变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初能变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初能变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生平事迹
独立之精神 , 自由之思想
初能变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 独立之精神 , 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初能变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初能变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初能变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初能变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初能变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此外,初能变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初能变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初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初能变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u2018有u2019,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u2018有u2019了;如果要证明它为u2018无u2019,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u2018有u2019,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u2018无u2019呢?”初能变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著作书目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金明馆丛稿二编》
《寒柳堂集》
《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
《论再生缘》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人物性格
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论语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却不作经学与三代两汉之学问。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初能变。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u2018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u2019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傅斯年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编年事辑》(略)
《石泉访谈录》: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产物,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编年事辑》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哀金源》、《青鸟》等诗可见其对蒋政权的失望与愤恨。
青鸟传书海外来,玉笺千版费编裁。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
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
《寄杨树达》诗,又可见出其对共产党的不合作态度。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
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
留命任教加白眼。
剩有文章供笑骂。
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突厥通考序》: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尺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与汴路运输之中断。其结论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其书四次遭劫: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
他人评价
绝世孤衷的畸人
《编年事辑》157:
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
《别传》: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编年事辑》引《吴宓日记》: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与友人论初能变
胡晓明来函言及近年有多篇文章论及初能变先生的生平志业与思想学术,一时颇成风气,青年学子遂以不知初能变为耻。这当中涵有复杂的时代思想发展线索,后来治思想史的人,不可不细加疏理。我以为此一现象的背后,可以反映出当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甚而中国知识人走向成熟的某种征兆。或是学统的索求与重理,或是价值的细审与重估,或是人格的提澌与感召,凡此种种,与前期相较,自有其意义。有人认为谈陈氏,只有讲其学术,才算是真知解,我以为不然。陈先生的学术文章,或有时而可商(前面有的且不论,近著如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就有批评陈先生论曹、马之争的观点“牵强”与“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如周勋初《当代学术思辨》亦记有当代学者对陈氏学术的批评,可参),然陈先生之精神世界,则旷世罕有其俦。我以为陈氏门墙广大,意涵极丰,只言其学术,或只言其思想,皆仅得其一端而已。
《初能变传》已经出版,作者搜访材料,用力颇勤,但读后感觉甚平浅,未能表出此老人格生命的复杂深邃与学术文章之精深广大。陈氏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学人,他的人格因素,竟是由一系列悖论构成,仅此而言,亦大有深意。请列举如下数端:
“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人物(他的学生中竟有人说他是所谓“晚清封疆大吏等高官家庭的子弟”,这是很可怪的),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寂寞销魂人”。
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1951年听说北京“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新书”,有诗云:
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迂叟(张之洞)《咏海王村》尝有“曾闻醉汉称禅瑞,何况千秋翰墨林”之句,海王村琉璃厂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陈先生可以说是由一叶落而知秋。
《赠蒋秉南序》: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从道德观点对宋学作了最高的礼赞。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将来之发展,必定是“宋学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
从文化理想对宋学作了最深刻的预言。
托命河汾。“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
《赠蒋秉南序》(1964)
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暇想而已。
人物观点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王国维与陈端生,一为殉中国文化“三纲六纪”背后最高之理境而死;一为欲摧破近代中国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然在陈先生看来,同为表现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与人格。此中深微处,惜乎汪《传》未能窥其蕴奥。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党家专政二十年,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寅恪对蒋家王朝已经完全看透,完全失望。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诗中常常流露出此川真实心情,如:“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以及“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销魂”,等等。他的诗,是一部现代知识人的可信可传的“心史”。
失明、膑足之际,仍能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如此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助手黄萱曾感慨:“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既“珍重君家兰桂室”,“裁红晕碧泪漫漫”(柳如是诗句),且讳深心苦,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也。
其历史观既注重经济动机,又注重精神动源。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与汴路运输之中断。其结论云:“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突厥通考序》:“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后者不易学,唯其如此,陈先生由学者进而哲人的境界。
其藏书有四次劫运: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陈先生的书劫,即陈先生的痛史。
陈先生真可谓“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先生如入《儒林传》,古今大儒失色;先生如入《文苑传》,天下文人黯然;先生如入《道学传》,大师让出一头;先生如入《隐逸传》,隐者奔走骇汗。先生究竟应归入哪一类人物,且置不论。以上种种,又当以“少喜临川”而“老同迂叟”、少游欧美而老著痛史、学贯中外而属命河汾(参拙文《寒柳诗之境界》),为此老一生大事因缘,方可得其荦荦大端。陈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这是了解陈氏内心世界的关键性的话。我辈阅人多矣。古今学人,牢骚、偃蹇、困苦、数奇,似未有如先生者。因而,作此传记之人,应依寅老《柳如是别传》文体,作知识人痛史写,不然,徒有其资料之排比,行状之考证,著述之提要,而精神与精神不能相贯通,意念与意念不能相融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汪《传》似不如蒋天枢《编年事略》,此意当细参。
来函论及寅老兼史家与诗人于一身。此正是他不可及处。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曾谓,史“叙述已然之事”,诗“则叙述或然之事”;“诗言普遍而历史则记特殊”。我国史学精神,则直追“天人之际”,力通“古今之变”,已由“特殊”而进于“普遍”。史亦可言“或然之事”,其大义即涵具于太史公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六字之中。钱锺书先生讲“史蕴诗心”,畅论史家可以“悬拟设想”、可以“想当然耳”,使后人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堪入小说、院本”(《谈艺录》,诚哉斯言,然惜乎钱氏只从文学之想象与虚构着眼,所见者小,似与太史公之“思来者”中所含蕴的“诗心”,尚隔一间。陈氏之史学,则于此大有会心与妙解。试举《柳如是别传》文例三证:
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能继续朱氏之残馀,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馀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
案:明言“至今”,即“述往思来”义。余英时说“由于这一隅之地已成为国际经济系统中的一环”,故不可谓不系“全国之轻重”于一隅。陈先生写出来的只有十之二、三,余下的须我们细加省思。这里且以当今文化经济战略格局更广而论之,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远东研究院院长汪德迈先生(Leon Vandermeersch)新著《新汉文化圈》所指出:“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同胞结合起来,海外华人就组成为一个5000万高质量的人类群体。这一群体不仅是连接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纽带,而且是恢复汉文化圈凝聚力的中介。他们属于这一文化圈,并将影响本区域的现代化进程。”此番话正可作一注脚,由此我们不得不叹服寅老神会智度之妙。
《别传》又云:
噫!三百五十年间,明清国祚俱斩,辽海之事变愈奇,长安之棋局未终,樵者之斧柯早烂矣。
案:“辽海”云云指韩战后的新局面。长安之棋未终,大有深意存焉。1945年诗云:“花门久已留胡马”,“收枰一着奈君何”;1948年诗云:“消得收枰败局棋”,寄寓有关苏俄觊觎东北的隐忧。但是,自韩战后,冷战局面终于形成(韩战的背景是美苏争夺亚洲霸权;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局面是汉文化圈整体最严重的创伤),中国之命运,与世界之局势相绾合(即寅老之著名文化史观点“外族盛衰连环”说),成为一“未终”之棋局。“烂柯”即表明世事变化极大极快。此四句话,正是诗心史笔浑然一体。寅老的感慨极深,他对于中国未来的关切心事与卓越见识,真是并世无二。
《别传》又云: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此一段文字,极具唱叹生情之妙,亦为研究陈先生的学者们常常引用,以说明《别传》的宗旨所在,但大都语焉未详,或不得要领。《别传》宗旨,可分说可合说。合说即陈先生“明清痛史新兼旧”一句便了。分说即“史”与“诗”两个层面。“史”的兴趣即寅恪一贯的知识兴趣,即求真,即为柳如是洗冤。作者往往在《传》中解决一段悬案,洗出一段清白之后,每每流露出莫大愉快:“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几人哉?更复几人哉?”“……真理实事,终不能靡灭,岂不幸哉?”等等。进而言之,陈先生下如许大功夫于辨诬、求真、沅冤,其深层心理,殊可深玩。倘若我们把陈先生心目中“阿云格调更无俦”的河东君视作中国文化命运的象征,倘若我们联想到古代文化、古典文学在当代中国遭“深诋”、受“厚诬”的命运,则我们亦可问道:“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陈先生的“绝世孤衷”者,“更复有几人哉?”自“诗”的层面说,即于求真,更进而求善求美。因而陈先生此段中“引申”一词,大可深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改男造女态全新”、“欲改衰翁成姹女”的时代,陈先生偏偏在他的文化世界中“著书唯剩颂红妆”。其述往思来的苦心即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明清易代之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二十万人皆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座中若个是男儿”、“今日衣冠愧女儿”。在中国文化的语义系统中,“女儿”之贞节乃士人之气节之一种象征,因而此气节问题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支柱,一旦抽掉此一支柱,士将不士。在1950年刊行,1955、1959年修订重印的《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先生说,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士大夫阶层之人,有贤不肖巧拙之分,其贤者拙者,常感痛苦,因其不善适应标准与习俗之变易之故也。这正是他一贯的思想。陈先生易此稿初名《钱柳因缘诗释证》为《柳如是别传》,又在第一章“缘起”中说:“今撰此书,专考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正是著书大义。而陈先生的预感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后来文革中知识分子的某些表现,正是知识人被摘除了灵魂之后的恶果。
诗人气质
初能变天性涵具诗人气质
有两条材料,可以说明。一是汪《传》引李潢语:“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p33)。二是钱穆《师友杂忆》记,钱氏于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幽居作《国史大纲》时,一日寅恪偕锡予(汤用彤)来此地一宿,曾在寺院中石桥上临池而坐,寅恪对钱穆言:“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是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这条材料极可宝贵。陈先生的气质,由此可以想象。他常云:“读史旧知今日事”,“世变早知原尔尔”。仔细想来他不仅天性涵具诗人的一份敏感,而且此一份敏感似超乎常人。譬如说他在童年时即预感到清廷的覆灭与天下的大乱。“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当读是集也,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环宇纷扰”(《赠蒋秉南序》)。查《编年事辑》:1901年陈家定居南京,1902年寅恪即赴日留学,他有此一预感时,年仅十一、二岁。如此颖悟善感,不可不谓出于天性。因有此一种天性,陈先生认为人事可以“前知”。三十年代初,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颇传于世。因呓语与当时世局若为符契,世人颇惊以为奇。陈先生不以为奇,撰《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一文,借摩尼教之语,说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而曲园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言多中,复何奇之有焉?”陈先生亦属“湛思而通识之人”,故能说出巳身之所遭遇,“在此诗(《呓语》)第二第六首之间”,至于第七首,则“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此亦可视为陈先生的一大预言。(参看钱仲联《清诗纪事》第十五册道光朝俞曲园诗有关注释)又,1966年《丙午元旦作》有句云:“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五个月之后,预言竟成现实!再往前讲,《赠蒋秉南序》作于“文革”前夕的1965年,今日回思其“气机触会”之际,此文句句可堪深玩。
抗日诗作
梦里匆匆两乙年②,竟看东海变桑田。
燃萁煮豆萁先尽, 纵火焚林火自延。
来日更忧新世局, 众生谁忏旧因缘。
石头城上降幡出③,回首春帆一慨然。④
①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为武汉、宜昌、沙市受降主官。
②两乙年,一指乙未年(一八九五),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不平等中日合约。一指乙酉年(一九四五)九月三日日本签订投降条约。
③石头城句,化用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句意。
④自注:“光绪乙未中日订约于马关之春帆楼。”
作品评论
近参加编选《中国文化百家文萃》,选近现代论文,一家一篇;于初能变文,选其《论韩愈》。兹简述其理由如下:
文化史
《论韩愈》云:
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明案:这是大判断,下得深切、准确。)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
案:一般论者只能着眼于以古文反对骈文的文体之争,仅仅着眼于文学史、批评史上的范围来讲古文运动的发生,更可笑者以骈文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以古文代表新兴中小地主阶级利益,非常别扭做作。
一般论者只从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去肯定“文以载道”说,只有寅老才看出了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即所载之“道”,乃是政治上的“尊王攘夷”,以及文化上的“尊儒排佛”。政治与文化之所以有现实的关联,是因为自安史乱后,唐代之藩镇多胡族或胡化之汉人。这样,“文以载道”之作为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其文化大义遂得以真实呈露。
我读了《论韩愈》之后,有一种想法,搞批评史、文学史的人,眼光不能太短浅了。
此文的文化史眼光又体现在作者将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准确定位,即中国文化前后两期转旧为新的关捩点之人物: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此一论断,下得大气磅礴。
辨证思想
我曾经见过不少选本,都选了韩愈的代表作《原道》。新选家们似乎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一方面肯定其“排佛”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无一例外地指责韩愈宣扬“唯心”,宣扬封建统治者正统的伦理思想,强调君主对人民统治的合理性。我们见惯了这种政治分析,就更觉得陈先生的史识的深刻。更糟糕的是,这种政治分析法还往往冠以“辩证”思维的名称。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自诩、传授这种虚假的“辩证法”而不觉其非。而《论韩愈》则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才算是真正的辩证思维。陈先生在此文中显示的一种辩证思维的精义,即看透事物之间“相反而适相成”的关系的一种智慧。
汪荣祖说:“从来儒者以韩愈排佛而钻研佛理,或讥之,或讳之,俱未悉伐异必须细究敌说之理。韩实以敌说为己用,以助阐道统,何妨其仍以儒学归心立命。”(汪《传》,此说语焉不详。实际上,在陈先生看来,不仅助阐道统,而且奖掖后学、匡救政俗、宣传学说、改进文体,皆与佛学有关,皆“以敌说助成己说”。这篇论文以韩愈排佛立论,彰显文化大义,然又以韩愈思想从佛学转出,发千年未发之覆。其妙处正在于相反相成,以圆而神之枢,运转、吐纳方以智之义,极富于真正的辨证思维意味。有此一法,学问全般皆活。这不是斤斤于材料之排比、真伪之考订的的学者所能措意的。
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
案:彼说可以助成己用,寅老自有其深切的现实关切存焉。参见同年(1951)写作诗句:“同酌曹溪我独羞,江东旧义雪盈头。”坚持“江东旧义”即“不负如来西来义”,即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犹是最高楼。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即表明对于异质文化主宰中国思想界的深忧。“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以及“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缘阴成幕听鸣蝉。”“蝉鸣”即极单调的声音,即对于学术文化定于一尊的讥剌。可见他的关心,乃是文化精神的方向。这不仅是写作《论韩愈》一文的心境,而且是陈先生一贯的文化观,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即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先生的终极关怀与他的现实关切,始终是不可分割的。
《别传》结束语: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广州赠蒋秉南》诗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别传》的动机:
余英时说:“借钱柳关系说去留问题”。其根据是:1,《霜红 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上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王”、“兴亡”兼古典与今典;“同入”,即感同身受,不是一般的读后感。2,《别传》第116883页,引张煌言《上延平王书》,明确说出“海外扶馀“不足以“王”,其古典即台湾的郑延平不足以王,其今典即今日流亡之政权不足以王。3,《别传》中寅老对于郑延平的一段分析,余英时认为是讲他自己的事:
寅恪案:郑氏之取台湾,乃失当日复明运动诸遗明之心,而壮清迁及汉奸之气者,不独苍水如此,……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自白茆港移居城内旧宅也。然河东君留居芙蓉庄,直至牧斋将死前始入城者,殆以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犹有可能,较之牧斋之心灰意冷,大有区别。钱柳二人之性格不同,此即一端,足以窥见矣。
其实,陈氏并无更多的寓意,只是讲明“钱柳二人性格之不同”。再联系到钱穆《师友杂忆》中记陈夫人赴港事失实,更可见余氏过于神经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