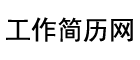玻尔兹曼的个人简介
路德维希·玻尔兹曼,1844年(甲辰年)2月20日--1906年(丙午年)9月5日),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奥地利物理学家。基本内容
路德维希·玻尔兹曼是奥地利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在气体的分子运动理论、统计力学和热力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做为哲学家,他反对实证论和现象论,并在原子论遭到严重攻击的时刻坚决捍卫它。
“如果对于气体理论的一时不喜欢而把它埋没,对科学将是一个悲剧;例如:由于牛顿的权威而使波动理论受到的待遇就是一个教训。我意识到我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与时代潮流抗争的个人,但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贡献,使得一旦气体理论复苏,不需要重新发现许多东西。”
―― 玻尔兹曼
玻尔兹曼的一生颇富戏剧性,他独特的个性也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关注。对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玻尔兹曼――笃信原子的人》一书([意]卡罗·切尔奇纳尼著,胡新和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7月版,30.00元),方在庆教授和关洪教授从不同的侧面做出了相应的评价,其中关洪教授着重提到的译文的质量问题,希望能够引起相关各方的注意。
有人说奥地利物理学家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1844~1906)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乡巴佬”,他自己要为他一生的不断搬迁和无间断的矛盾冲突负责,甚至他以自杀来结束自己辉煌一生的方式也是其价值观冲突的必然结果。也有人说,玻尔兹曼是当时的费曼。他讲课极为风趣、妙语连篇,课堂上经常出现诸如“非常大的小”之类的话语。幽默是他的天性,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自视甚高与极端不自信的奇妙结合――对这位天才的心灵损害极大。本书作者用了一个副标题:“笃信原子的人”,又给玻尔兹曼画出了另一个侧面像。
如果我们摈弃具有严格“决定性”色彩的“社会建构论”,而采用一种较为“软弱”的立场,试图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文化组成中寻找一些相关因素去“解读”玻尔兹曼,应该还是可行的。玻尔兹曼的“父国”处于当时被称为“多瑙河畔的中国”的奥地利。奥匈帝国外表上极其强盛,但内部矛盾重重。在学术界,人们常常为一些繁文缛节而浪费时间,不断的文牍折磨着疲倦的学者,遵从一定的礼仪“程序”比具体的事情更重要。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教授阶层尽管地位不低,但并不属于最受尊敬的阶层,退休后还得为没有着落的养老金发愁。
玻尔兹曼出生于维也纳,在维也纳和林茨接受教育,22岁便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就有好几个大学向他提供职位。他曾先后在格拉茨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以及莱比锡大学等地任教。其中曾两度分别在格拉茨大学和维也纳大学任教。
在玻尔兹曼时代,热力学理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他在使科学界接受热力学理论、尤其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通常人们认为他和麦克斯韦发现了气体动力学理论,他也被公认为统计力学的奠基者。
按理说,玻尔兹曼的学术生涯应该很平坦,可事实上却充满了艰辛。其中有不少是社会的因素,但更多地应该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
玻尔兹曼与奥斯特瓦尔德之间发生的“原子论”和“唯能论”的争论,在科学史上非常著名。按照普朗克的话来说,“这两个死对头都同样机智,应答如流;彼此都很有才气”。当时,双方各有自己的支持者。奥斯特瓦尔德的“后台”是不承认有“原子”存在的恩斯特·马赫。由于马赫在科学界的巨大影响,当时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也拒绝承认“原子”的实在性。后来大名鼎鼎的普朗克站在玻尔兹曼一边,但由于普朗克当时名气还小,最多只是扮演了玻尔兹曼助手的角色。玻尔兹曼却不承认这位助手的功劳,甚至有点不屑一顾。尽管都反对“唯能论”,普朗克的观点与玻尔兹曼的观点还是有所区别。尤其让玻尔兹曼恼火的是,普朗克对玻尔兹曼珍爱的原子论并没有多少热情。后来,普朗克的一位学生泽尔梅罗(E. Zermelo)又写了一篇文章指出玻尔兹曼的H-定理中的一个严重的缺陷,这就更让玻尔兹曼恼羞成怒。玻尔兹曼以一种讽刺的口吻答复泽尔梅罗,转过来对普朗克的意见更大。即使在给普朗克的信中,玻尔兹曼常常也难掩自己的“愤恨”之情。只是到了晚年,当普朗克向他报告自己以原子论为基础来其推导辐射定律时,他才转怒为喜。
玻尔兹曼沉浸在与这些不同见解的斗争中,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尽管玻尔兹曼的“原子论”与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之间的论战,最终玻尔兹曼取胜,但这个过程对于一个科学家的生命来说,显得太长了。玻尔兹曼一直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他曾两度试图自杀。1900年的那次没有成功,他陷入了一种两难境界。再加上晚年接替马赫担任归纳科学哲学教授,后几次哲学课上的不大成功,使他对自己能否讲好课,产生了怀疑。
玻尔兹曼的痛苦与日俱增,又没有别的办法解脱,他似乎不太可能从外面获得帮助。如果把他的精神世界也能比作一个系统的话,那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按照熵增加原理,孤立系统的熵不可能永远减小,它是在无情地朝着其极大值增长。也就是说,其混乱程度在朝极大值方向发展。玻尔兹曼精神世界的混乱成了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他最后只好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其“混乱程度”不断增加的精神生活。1906年,在他钟爱的杜伊诺Duino,当时属于奥地利,一战后划给意大利 ,他让自己那颗久已疲倦的天才心灵安息下来。
这就带来了一个学术界熟知,但绝非是无可争议的“普朗克定律”。其表述如下:“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照例不能用说服对手,等他们表示意见说u2018得益匪浅u2019这个办法来实行。恰恰相反,只能是等到对手们渐渐死亡,使得新的一代开始熟悉真理时才能贯彻。”对普朗克来说,学术争论没有多少诱惑力,因为他认为它们不能产生什么新东西。
由于上述说法后来又被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学者,如托马斯·库恩等多次引证,它似乎成了一条自明的真理。果真如此吗?如果普朗克所言不虚,那么科学争论在科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普朗克为人平和、正直,被誉为“学林古柏”,其高尚的人品是值得人们敬仰的,但并不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哪怕这句话多次被人们引用。附带说一下,普朗克还说过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话:“女子从事学术研究是与她们的天性相违背的。”这句话当然也是大大值得商榷的,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都不会赞成普朗克的这个偏见。
尽管玻尔兹曼的传记已有多本,但这本书还是有一些特色,出版后得到了国外学界的一致好评。主要的物理学期刊都发表了书评,而且总体肯定的比较多。科学史的权威刊物Isis也发表了J.R.Dorfman对此书的较高评价。阿拉斯代尔·厄奎哈特所写的书评,对此给予较高的评价见《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8日科技视野版 。Pul F.Zweifel写道:“切尔奇纳尼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水平是非凡的。人们会惊讶,在人的一生中,如何能读完他所提到的所有那些书和文章。” Zweifel也提到了书的不足,那是对原著的英文句法方面而言的。作者曾自己将一些德文句子按德文的句式翻译成了英语。(可参见http//www.pzweifel.com/music/boltzmann_secondo.htm)
玻尔兹曼的外孙、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Dieter Flamm,在《物理世界》(Physics World)1999年4月号上对本书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文末提出“我热烈地向所有对科学史感兴趣的人推荐此书”(见http://physicsweb.org/article/review/12/4/1)。此外,本书对玻尔兹曼之前和之后的物理学以及玻尔兹曼自己的贡献也做了比较清楚的描述。关于玻尔兹曼在哲学上的影响,作者也梳理得较为清楚。全书基本上没有那些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的数学公式和推导,一个学过《大学物理》的读者就能看懂。对于那些没有任何理科背景的人来说,本书第一章:“玻尔兹曼小传”约占五分之一的篇幅 是一篇完全用事实说话,而又以一种对玻尔兹曼充满同情和理解的笔调写成的传记。患得患失而又不失为性情中人,玻尔兹曼的天才形象活生生在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果你想了解玻尔兹曼有多风趣,玻尔兹曼自己写的漂亮的游记:《一个德国教授的黄金国之旅》作为本书附录 ,则是一篇不能不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