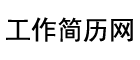邓一光的个人简介
1956年8月生于重庆市,蒙古族。祖籍湖北麻城。曾赴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工人、新闻记者、文学刊物编辑,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现为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文学院院长。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家在三峡》、《走出西草地》、《我是太阳》、《红雾》、《组织》、《想起草原》、《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亲爱的敌人》,小说集《红色贝雷帽》、《孽犬阿格龙》、《遍地菽麦》、《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她是他们的妻子》、《猜猜我的手指》、《远离稼穑》,诗集《命运风》等。作品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冯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等。个人简介
1956年8月生于重庆市,蒙古族。祖籍湖北麻城。当过知青,工人,新闻记者,自由写作者,文学刊物编辑,现为武汉文联专业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市文学院院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从事小说的写作。著有长篇小说7部;中篇小说三十余部;短篇小说三十余部;电视剧剧本三部;出版有《邓一光文集》(四卷本),各类文学专著二十余部。作品多次被选载、介译到海外及入选各种版本的年选。
主要作品
诗集《命运风》(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短篇小说集《红色贝雷帽》(海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篇小说集《孽犬阿格龙》(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长篇小说《家在三峡》(武汉出版社1996年出版)
长篇小说《走出西草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出版)
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长篇小说《红雾》(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
长篇小说《组织》(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出版)
长篇小说《想起草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中篇小说集《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北岳出版社2000年出版)
文集《邓一光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中篇小说单行本《远离稼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长篇小说《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电视剧本《城市星空》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
散文集《脚下地图》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中篇小说单行本《孽犬阿格龙》(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艺术随笔集《从大地走向大地》(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
电视剧本《江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中篇小说《亲爱的敌人》
《我是太阳》由都梁编剧,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出,反响不错。
作品获奖情况
中篇小说《孽犬阿格龙》获武汉首届文艺基金奖。
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小说选刊首届最佳优秀作品奖、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上海市第三届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武汉市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首届湖北文学奖荣誉奖、武汉市黄鹤文化奖、首届湖北省少数民族文学奖荣誉奖。
长篇小说《家在三峡》获武汉市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武汉市文艺基金奖。
电视连续剧《家在三峡》获中宣部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广电部第16届飞天奖、湖北省五个一工程特别奖、武汉市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长篇小说《我是太阳》获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第三届人民文学奖、全国十佳长篇小说奖、屈原文学奖;入选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建国五十周年五十项献礼作品;中国作家协会十部献礼长篇小说嘉奖、武汉市五个一工程特别奖、武汉市文艺基金特别奖、首届湖北文学奖荣誉奖、首届湖北省少数民族文学奖荣誉奖。
中篇小说《大妈》获第二届人民文学奖。
中篇小说《远离稼穑》入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998年度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排行榜、获武汉市文艺基金奖。
短篇小说《狼行成双》获小说月刊第8届百花奖、全国十佳短篇小说奖。
长篇小说《组织》获首届湖北文学奖。
中篇小说《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获第七届十月文学奖、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入选当代文学最新作品2000年下半年排行榜作品。
长篇小说《想起草原》获湖北省图书奖提名奖、湖北省政府奖提名奖。
散文《军属》获第十一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复评暨2000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金奖、天津市新闻一等奖。
散文《母亲的巴掌》获全国报刊副刊奖。
散文《这世界美丽如树》获长江文艺散文随笔奖。
本人获首届冯牧文学奖、湖北省文艺明星奖、武汉市黄鹤文艺奖
2011年3月,《我是我的神》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成长历程
因痴迷读书挨打邓一光说他生在一个军人家庭,这样的家庭不喜欢孩子读课外书,父母特别反对孩子读小说,他们担心那些书会让孩子脱离主流话语,更不喜欢孩子读书读到迷迷瞪瞪的。在父亲退休之前,他很少见到父亲,他对父亲在那个时期最深刻的记忆主要是父亲送给他的耳光。从小学到初中,他是在父亲的“内部读物”中读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父亲根本不让他读,他因为经常偷偷读书,挨过父亲的不少打,但他有自己的办法,早早地躲进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书,然而父亲总是能恰巧在他躲在被窝里看得入迷时,狠狠地掀开被子,把他拖出来煽耳光。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远离书籍,反而把读书作为自己生活的重要部分。
父母给他的零花钱那时大多数都让他花在看小人书上了,他上小学时读的是寄宿学校,星期六放假,如果父亲没派车来接,他就常常和姐姐省下乘公交车的八分钱,去书摊上看小人书,然后怀着对小人书的无比思念,走很远的路回家。
如果不算小人书,他应该是从小学三年级才开始读第一本课外书,那本书就是《红岩》。邓一光说,那时他就身在重庆,书上写的又是重庆的事,很有现场感,用他自己现在的语言来说,这本书写了一群隐匿了真实身份的反体制者的生死故事,相当符合他当时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的阅读心态,这本书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以后,他又一股脑儿接着读了《青年近卫军》、《铁木尔和他的伙伴》、《牛虻》等小说。当他读到小学四年级时,“文革”开始了,他当红卫兵的哥哥从图书馆抢回不少书,这些书大多是苏俄文学和法国文学之类的书:《白静草原》、《人间喜剧》、《叶尔绍夫兄弟》、《罪与罚》、《红字》、《十日谈》、《一千零一夜》、《罗亭》等。适逢那个特殊年代,重庆武斗盛行,为避流弹,他就安然地躲在桌下,一本一本地贪婪地读完了那些书。夜里要是停电,他就想办法点着矿石灯读,头发因此烧了不知多少根。虽然烧掉了些头发,但是他收获了对这个世界的一些新认识,他知道了这个世界不光是身处的世界,还有别的内容,比方说,武斗是杀人,是暴力,是恶对恶,而书中讲述的大多是人的柔软和善良,这种现实与书中世界的反差,应该是人对另一个世界的幻想的初衷。
对成长期处于大变革大动荡中的孩子,书给了他另一个世界,只是,他当时无法知道那是虚拟的,他不知道人是有幻想的要求和能力的,可是,书中展示的丰富和温暖让他幼稚的心灵远离了现实中的冷漠世界。他从此深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并不是一切,还有另一个一切、若干的一切在不知道的地方,可以从书中找到。
1974年,他高中毕业后下乡来到重庆开县当知青,与其他知青不同的是,他带着书下乡,其中的马列著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读了好几遍,不求甚解,他就背一些激烈段落,和人辩论时用上一些,常常特别管用,效果是能出奇制胜。
对下乡生活的回忆还是跟书有关的最有趣。当时的大队磨面房收了一些农民家里的旧书,用来包挂面,他就拿马列著作换回旧书,自带的马列著作换完了,就拿保命的口粮麦子换。他下乡的地方是山区,土地稀缺,一年分六七十斤麦子就不错了,他一米八的个子就全靠这些宝贝支撑了,可是,为了换回自己想看的这些旧书,哪怕很心疼也还得换。
队里有一个会计,家中有一些旧书,线装本,《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庄子南华经解》、《又玄集》等这类古文书,读起来十分生涩,但无书可读的日子更生涩。那些书在煤油灯下伴他度过四年,如今仍保存在他的书橱里。
他老找会计借这些生涩的书,有时还回去再借,因为没书看憋得慌,后来会计把家里的书全送他了。会计和他全家人因此成为他在队里最尊重的人,会计一家人斯斯文文,衣裳补丁摞补丁,洗得干干净净,说话笑眯眯的,从不说粗话,到底是有藏书的家庭啊。
书奇缺的年代,也是手抄本流行的好时光,他当然是读过一些的,印象最深的是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字抄得娟秀,工工整整,老厚一摞,读时老怕把纸翻破了,要小心翼翼。一个朋友送了他一本手抄的泰戈尔的《飞鸟集》,他一直珍藏着。
1978年,回到重庆市,他当上了工人,书不知为什么莫明其妙地开始被禁。新售的书总是少而又少,每出一种,人们就奔走相告,报纸也登消息,用的还是很显眼的字号和标题。新华书店比总理府热闹,谁认识书店员工比认识外星人还要不得了。书首发的当日,他就和同事约好,谁当天不上班谁起早,凌晨去书店门口排队。他排过两次队,买什么书忘了,有一次凌晨两三点钟去,前面有上百人,还挤,挤出一身臭汗。第二次不到零点去,仍未排到头十名。售书数量有限制,好像每人不得超过三册。书店员工大声喝斥,比宪兵还厉害。有人在书店门口打架,有人因排队买书恋爱了。荒唐而真实的年代!他至今还这么感叹当时的求书激情。
直到后来,书的出版市场活了,他自己的许多条件也改善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特别有意思的求书经历了,书越来越多,自己也变得挑剔了。
书是生活必需品也许天生就爱书,也许天生就离不开书,邓一光说,书是他生活的必需品之一,每天都会读书,但不像一日三餐那么刻板,什么时候想读了,抓起来就读,随心所欲地读。有时读着打盹了,也不硬把眼皮子支起来,干脆顺势睡上一觉。他经常是到手的书未必读得完。大多数书是不会全部读完的,主要是中途没兴趣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尽管是读书人读书,家里也有很好的书房,可是他读书从不在书房里,主要在床上,有时候在沙发上。尽管有一把躺椅是专为读书添置的,但他还是喜欢躺着读书。他曾经在书房里放了一把躺椅,拿着书躺在椅中读过几次,也没觉得有多大意思,就把躺椅搬出了书房。
他说自己是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读书的姿态也不是那么坐在书桌前循规蹈矩地读,他只在一种情况下坐着读书,那就是人在旅途的时候,否则基本上是躺着读,管他眼睛坏不坏。
有人问到他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常读的书目或品种有哪些,他不客气地说:“没有,那是世界上最傻的问题!”他选择读什么书,要看他处于什么心态,基本上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没有什么目的性,比如前些日子,他对心理问题感兴趣,就读了班克特的《东西方心理治疗的历史》、罗杰斯的《个人形成论》、恩普森的《眨眼与做梦》。又比如再前些日子,他是随手抽出法布尔的《昆虫记》,其中的《红蚂蚱》那一册,读得特别开心,就连读了好几册。
邓一光的书读得很杂,难以归类。他家里有七个书柜,其中三个书柜里是小说,其他四个则门类繁多,什么书都有。近年来,他对小说反而不似十年前那样热衷,只有很少量的国外小说才会一直看下去。偶尔翻到曾读过的旧小说,一旦读进去了,也会再读一遍。
任何一本书,对于他来说没有名家之作一说,只有他喜不喜欢的区别。一般来说,他不喜欢的书是传记,可能也有不错的传记,比如,传记作者写自己的,应该是比较有味道的。但是,大多数传记作者都远离传记中的主人公,自说自话,读这一类书实在是让读者受害。
为自己而写作在邓一光的获奖作品《我是太阳》中有这么两段话:“他们是太阳,真的太阳!没有什么能击倒他们!就算击倒了,第二天黎明,他们还会不屈不挠地升起来,继续燃烧他们的命!”这也许就是邓一光本质的写照,他是“一个勇敢、坦率、不顾一切、信念专一、执著而具备超凡的爆发力和韧性”的邓一光。邓一光的母亲是蒙古族,他的血统里多少继承了蒙古人的特性,他的很多作品都喜欢以草原为背景,他特别喜欢马。
他的写作就像他本人一样极富个性,“写作就是我的呼吸,跟别人没有关系,我是为自己而写作”,他对我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视写作是另一种生命,如果没有写作,他几乎不能想像他会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著有《我是太阳》、《想起草原》等8部长篇小说,《父亲是个兵》、《狼行成双》等数十部中短篇小说(其中30余部中篇,40余篇短篇),出版了《邓一光文集》。他的作品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屈原文学奖等诸多大奖。其中《父亲是个兵》、《战将》、《远离稼穑》、《我是太阳》等,又被人们称为邓一光的战争文学谱系,这一系列的作品展示了邓一光在文坛的强大实力。他自己也曾经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人。”邓一光就是这样,哪怕是友人之间的闲话,也能表现出他鲜明的个性和深沉的魅力。
邓一光的写作有时很疯狂,38万字的《我是太阳》只用40天就写成了,这还是他用笔写的,完全没有电脑键盘帮忙。
邓一光始终宣称,他是为自己写作,他不想了解别人喜欢看什么样的文字,自己想写什么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下去。他只写自己喜欢写的作品,当写作完成时,写作的快乐就已经结束了,至于这部作品是否受读者欢迎、是否有卖点、能赚多少钱,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跟他的写作过程也不再有任何关联。因此,他没有必须不考虑自己的喜好而去迎合别人的口味。他的写作是不关心市场的,尽管现在各行各业都很重视市场的反应。
很多事情,他并不去追赶潮流,甚至想回到昨天。近期,他正在赶一部80万字的长篇,三个月没理发,家里人已经习惯了他的一切,他不以为然地说,无非就是头发盖住了耳朵,原始人还留长发呢,不理发也只不过是暂时回到昨天。
如今,当中国已经有一亿多网民时,他还是不上网,朋友给他申请的一个电子邮箱,他一年只用了十几次,他对自己不熟悉的网络世界不愿置评,却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守旧或传统的人。
除了喜欢阅读和写作之外,邓一光还非常热衷于行走,他每年都会有一个月或几个月的时间外出旅游。去感受森林、草原、大海、高原、沙漠,他甚至说他的家乡就是大海。
作家形象
硬汉形象一个冬夜,邓一光说,他的小说是粗糙的。这里大约包含着两个意思:一个是说,他对自己的很多小说都不大满意,甚至包括获了奖的。比如说《我是太阳》,他现在还是遗憾,他反复对自己说不应该那样草率就交上去,如果再改一遍会更好些;另外一点,他的字很难辨认,他的第一个小说发表在《芳草》上,当时是编辑重新抄了一遍才交到照排的,并不是他不想写清楚,只是“感觉来到”的时候,心急似火。他形容说,那就像你从大海里向回游,眼看就要到岸上了,一排排的浪头打过来,令人绝望而恐惧。
说起水,朋友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武汉有个叫吉庆里的地方,一个三教九流聚居的地方。2000年的腊月天,伙同一群朋友,邓一光去吉庆里喝酒。席间一位新识的朋友问,现在去游泳,敢不敢?可能是感觉到了挑衅的意味,一光盯着他的眼睛说,好!
于是一行几人打车到了滨江公园。夜正寒,漆黑得不见五指,公园里没有人,只有长江大桥在远处冷冷地坐定。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一光在前面,边走边脱衣服。走在后面的人开始算了算了地劝说。只听见咕咚一声,一光就不见了。爬上江间的趸船时,一光感觉身后还有一个人,一看是摄影家郭立。岸上的人开始着急了,正嚷嚷着要找人来救的时候,两个人已经笑着擦身穿衣了。先前提议的那个人一声不响的把车停到了他的身边,一光却自己打车走了。他没有生那人的气,甚至有些感激他。入水的瞬间,他感到了极大的快乐,一种痛苦后的快感。
一光出门习惯走路,在城市里他打车。一光的太太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两个人感情很好,因为“互相能够包容”。一光的儿子是个车迷,对各种车的品牌性能如数家珍。有一段时间,太太和儿子的话题总是最后落到车上面。一光是个读书人,以写作为生,并没有很多积蓄。于是他开始接电视剧的活儿。电视剧的活儿于作家来说,就如同钢琴家在酒店大堂弹琴,于专业的提高并无帮助,所以大多数作家都不会真正热爱做电视剧的编剧。有一天,邓一光把一个信封交给太太,说买辆车吧。太太是个时髦的人,选了时下最经典的家轿“小别克”赛欧,很漂亮的白色。太太欣喜之余并未忘记承诺,下次你出门,我可以开车送你去机场。一光笑。出门照旧打车。
不做现代人邓一光常常为电脑发愁,我曾经为此嘲笑了他,说他不是个现代人。之后我觉得自己很残忍,因为我读到了他的一篇关于电脑的文章。
“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要是不学会电脑,就只能停滞在20世纪这一头,没有资格进入21世纪。我想我又不是不努力,凭什么就不能到21世纪里看一看。”邓一光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开始了自己的网络生活。他这样描述网络:“一只饿着的狼,它明知道有陷阱,明知道有猎枪,明知道它和村子里的那些生命,不可能有沟通,明知道它在最后,不会是村子里那些生命的对手,明知道如果冲突发生,灾难不光只降临到它身上,还会殃及雪松、桧柏、牵牛花、松萝、白唇鹿、狍子、狗熊、狮子、水螅、蝴蝶、飞鸟、土拨鼠和风……它仍然会一步一步地走近村子。”然而,他还是有了自己的决定:“我肯定会上网的,做一条网中的鱼儿。”
有点前后矛盾,更有无奈和惆怅,但这些都是在一种被称之为“困惑”的原动力之下发生的。邓一光说,正是困惑让人活下来。困惑让人去置疑什么,挑战什么,征服什么。
其实说邓一光不是现代人的确不公正。对都市,他有着独特的感知。他还曾经劝说我,别错过城市里最美好的瞬间。我问是什么?他说是日出。我笑,他听出我笑中不屑的成分,并没有生气。很认真地说,城市的早晨很脏,有很多不协调的东西,然而,太阳出来的时候,极大的透明度让一切都和谐了,于是城市醒来。对他来说,真正的精神家园是自然界,因为城市给人的是一颗坚甲累累的心。
他聊天的题目多半是在自然界徘徊,或者绕来绕去,还是回到原点。当他描述草原上冰冷的泪水的时候,描述挂在枝头由青转红的枣子的时候,描述那木措变化多端的湖水的时候,听的人很难不感动。不是因为他状景的能力,而是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有值得敬重的部分,何其幸运,他感知并拥有了它们。有一次,话题是生物界,他说,生物界的很多动物植物经常有意将自己弄伤,以激发自己的抵抗力和生命力。
我猜想,他那样有朋友缘,多半是因为他的思考方式“怪有意思”。
文学孤儿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作“加沙”的感觉并不太好。一光的母亲说,你脸上的肉是竖的。一个不会笑的孩子。
七十年代,怀着青春的犹豫,邓一光到胶东下乡当知青。和别的同学不大一样,他是抱着一种“与家庭决裂”的想法,所以当别人问起他的时候,他告诉别人,自己无父无母。当地的老百姓淳朴善良,邓一光被称为“孤儿老邓”。
也许这种孤儿情结使得邓一光的小说变得独特而忧郁,他最喜欢的短篇小说《狼行成双》讲的是一对狼夫妇的故事。故事的结尾令人伤感。男狼为了保全自己的“爱人”而碰死在枯井中。女狼消失在两个孩子的猎枪下,毛色妩媚。在短短的故事里,你看到了什么呢?爱情,人与自然,人性和兽性……语言的张力。
邓一光认为文学和批评是不一样的。批评的武器是梳理,而文学是无形的无框架的无序的。作家的权利是置疑,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革命。批评家和文学家共同面对潮流并抵抗潮流时,是同一种姿态。一个人在面对世界的时候,是有很多承诺的,而作家靠想象来反对承诺,表达自己的恐惧和怀疑。
邓一光说自己个性极端,不严谨,容易得罪人。邓一光有很多“中途逃走”段子。多年以前,邓一光应邀参加一个笔会。第一天,安排上庐山,天下雨了。“庐山不欢迎我啊”,在山顶上一光这样想。当时夜色低垂,他突然感到难过,原因不详。他拿起行李就走。
率性而为,在森林里在大海中在沙滩上都没有多大的问题,但在人群中就不行,这让邓一光迷惑。所以,他更喜欢独处。
我和一光的再度接触,是因为去西藏的事。我们用电话联络,商量细节,但更多的还是用电子邮件。他的心很细而且善良。他给我的电子邮件,内容是:关于西藏若干常识问题的扫盲。
几乎就要动身了,行程却突然被推迟了,因为一光的眼睛。他的眼睛在上次去西藏时出了问题。他的视网膜萎缩,医生禁止他去西藏。其实,医生还禁止他用电脑。知道这些,我的心有很痛的感觉。
通常别人是这样介绍他的:“邓一光,蒙古族,1956年8月生于重庆市,当过知青、工人、新闻记者、文学刊物编辑,现为武汉文联专业作家、文联副主席。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大姨》、《家在三峡》、《遍地莜麦》、《走出西草地》等小说。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并被翻译到国外。”客观,但有点冷。这与实际的他有着很大的不同。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一光有口音,话尾总有个“沙”字。电话中,他的声音很好听。有几次,他在路上,一边指挥司机进胡同,一边说我是救火。我知道一定是他的朋友出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