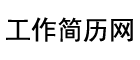陈名夏的个人简介
陈名夏(1601~1654)明末清初官员。字百史,江南溧阳(今属江苏常州溧阳)人。崇祯十六年廷试第三名(探花)),官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福王时,投靠入京的李自成。清顺治二年降清,以王文奎荐,复原官,旋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累官秘书院大学士。以徇私植党,滥用匪人,后因多尔衮追论谋逆,为宁完我所劾;与刘正宗共证名夏揽权市恩欺罔罪,受株连被劾论死。其诗文有名于时,著有《石云居集》十五卷,诗集七卷。生平简介
明崇祯十六年(1643)杨廷鉴榜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复社名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户兵二科都给事中。陈名夏好诗文,曾在山东、河北等地游学。喜结天下名士,为诸生时已名重天下。北京城破前十天,陈名夏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上吊自杀未果。王姓山西秀才力荐名夏加入大顺政权,入宏文馆(翰林院)。福王时,因降李自成定入从贼案。
降清后,保定巡抚王文奎推荐,复原官,超擢吏部侍郎。顺治八年,张煊弹劾他“结党营私”,陈之遴奏劾他“谄事睿亲王(多尔衮)”。 顺治十一年(1654)因倡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为宁完我所劾,第二天三月初二中午,顺治帝亲自讯问,侍臣当众宣读宁完我的劾奏,不等侍臣读毕,名夏极力辩白。帝大怒:“即使要辩解,为何不等宣读完毕?”命陈名夏跪着与宁完我对质。三月初三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御史陈秉彝替名夏缓颊,双方争执不下。刘余谟喋喋不休,帝为之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继续进行。陈名夏被转押吏部,至十一日吏部主张论斩。十二日,改绞死。临死前向门客柳生说:“我色竟不动也。”陈名夏之子陈掖臣被押到北京,杖四十,流放东北。
陈名夏死后,是年冬天顺治帝游南海子时,曾向冯铨称美陈名夏,说:“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冯铨则回答:“陈名夏于举业似所长。余亦易见。”谈迁说他“性锐”,然“肮脏”,好为名高。著有《石云居士文集》十五卷。
清史稿文载
陈名夏,字百史,江南溧阳人。明崇祯进士,官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降李自成。福王时,入从贼案。顺治二年,诣大名降。以保定巡抚王文奎荐,复原官。入谒睿亲王,请正大位。王曰:“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旋超擢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师定江南,九卿科道议南京设官。名夏言:“国家定鼎神京,居北制南。不当如前朝称都会,设官如诸行省。”疏入称旨。三年,居父丧,命夺情任事,请终制,赐白金五百,暂假归葬,仍给俸赡其孥在京者。五年,初设六部汉尚书,授名夏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八年,授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兼太子太保。名夏任吏部时,满尚书谭泰阿睿亲王,擅权,名夏附之乱政。睿亲王薨,是夏,御史张煊劾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下王大臣会鞫,谭泰袒名夏,坐煊诬奏,论死。语详煊传。是时御史盛复选亦以劾名夏坐黜。迨秋,谭泰以罪诛,九年春,复命王大臣按煊所劾名夏罪状,名夏辨甚力。及屡见诘难,词穷,泣诉投诚有功,冀贷死。上曰:“此辗转矫诈之小人也,罪实难逭!但朕已有旨,凡与谭泰事干连者,皆赦勿问。若复罪名夏,是为不信。”因宥之,命夺官,仍给俸,发正黄旗,与闲散官随朝,谕令自新。十年,复授秘书院大学士。吏部尚书员缺,侍郎孙承泽请以名夏兼摄,上责承泽以侍郎举大学士,非体。翌日,命名夏署吏部尚书。上时幸内院,恒谕诸臣:“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名夏或强辞以对,上戒之曰:“尔勿怙过,自贻伊戚。”诸大臣议总兵任珍罪,皆以珍擅杀,其孥怨望,宜傅重比。名夏与陈之遴、金之俊等异议,坐欺蒙,论死,复宽之,但镌秩俸,任事如故。
十一年,大学士宁完我劾之,略言:“名夏屡蒙赦宥,尚复包藏祸心。尝谓臣曰:u2018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u2019其情叵测。名夏子掖臣,居乡暴恶,士民怨恨。移居江宁,占入官园宅,关通纳贿,名夏明知故纵。名夏署吏部尚书,破格擢其私交赵延先,给事中郭一鹗疏及之,名夏欲加罪,以刘正宗不平而止。浙江道员史儒纲为名夏姻家,坐事夺官逮问,名夏必欲为之复官。给事中魏象枢与名夏姻家,有连坐事,应左迁,仅票俸。护党市恩,於此可见。臣等职掌票拟,一字轻重,关系公私;立簿注姓,以防推诿。名夏私自涂抹一百十四字。上命诰诫科道官结党,名夏擅加抹改,其欺罔类是。请敕大臣鞫实,法断施行。”疏下廷臣会鞫,名夏辨诸款皆虚,惟“留发复衣冠”,实有其语。完我与正宗共证名夏诸罪状皆实,谳成,论斩,上命改绞。掖臣逮治,杖戍。
部分诗选
五子咏·滇南唐大宋
苍山不可极,英特应地符。弱冠豪素,足迹凌寰区。 旁皇恣冥探,谐笑归吾庐。岂怨知者寡,灌园道有余。
五子咏·桐山方密之
方生天下士,踔厉青云端。独袂挥众言,河汉下飞湍。
宣籁匹金石,文陛相盘桓。一朝黄鹄举,流盼伤羽翰。
五子咏·沛县阎古古
歌台大风起,儿童吟乐章。逶迤数千纪,作者称登堂。
正声破淫哇,取材齐柏梁。男儿意气重,醉卧多尤伤。
五子咏·吴江沈元子
布衣颇不贱,视我隐侯裔。三箧暗能诵,贵游争交知。
山川助贫窭,乃欲安蒿藜。岁暮长安道,著书新满帷。
五子咏·滇南苍雪
侧闻演象教,乃在吴门山。日夕咏四始,策足开心颜。
家逾一万里,天空鸟飞还。同予念唐子,惨澹禅灯间。
西洋汤道未先生来
一日两命驾,过我松亭前。执手慰老颜,不若人相怜。
沧海十万里,来任天官篇。占象见端委,告君忧未然。
忠爱性不移,直谏意益坚。贾谊遇汉文,治安书可传。
公为太史令,洛下诚并贤。翻愧畴昔交,势利多扳缘。
愿从学道术,寡营成大年。
福宁州城外即事慰袁生
书生携我城外山,童仆举火何其难。流萤入户光自照,蟋蟀在床鸣不闹。
予家既破牛马走,世上饥寒无不有。何人共此患难中,与君且醉重阳酒。
孔融既逝宾客稀,丈夫熟视何所为。素秋零落色不瘁,纷纷轻薄皆小儿。
我欲歌,听者疑。我重泣,如绠縻。以此叹息无古道,千载相思在管鲍。
郊坛恭纪
霄汉星悬卤薄飞,泰坛火候龙衣。连钱苑马齐金勒,作阵宫乌历翠微。
日景吹葭寒谷暖,云光绕仗羽林围。侍臣恭赋横汾祀,群望黄舆紫陌归。
至睢州有感
寒山凄绝暮烟斜,旧日村原见几家。草长甫田惊宿雉,人稀落木乱啼鸦。
畏兵相避真如火,携友长征未有涯。夙慕中原文献地,到来拂面起尘沙。
文人性格的仕途悲剧
文人当官,古来与之。特别是 科举制盛行以来,八股取士,文人多活跃在政治舞台。陈名夏,也不例外。他是江南才子,崇祯十六年廷试第三名( 探花)),官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福 王时,投靠入京的 李自成。顺治二年降清,以王 文奎荐复原官,旋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累官秘书院大学士。可谓历经明、 大顺、清三朝政治风云,应有一定的当官经验了,可怜最终还是文人的性格让他五十多岁,以徇私植党,滥用匪人为 宁完我所劾,处以绞死。“我欲歌,听者疑。我重泣,如绠縻。以此叹息无古道,千载相思在管鲍。”明末清初是 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段,陈名夏恰恰处在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皇帝多疑,宦官专权, 文官弄术,武官要君,满汉相争,南北不容,明不聊生,社会动荡。陈名夏也算脑子很活的人,政治上很敏感,善于 投机钻营,懂得生活得复杂远远胜于生命。他在清初,既能与 摄政王 多尔衮的红人谭泰搞好关系,也能与顺治皇帝的重臣索尼结好友情,还大胆劝说多尔衮篡位,虽遭拒绝,却也因此受到多尔衮的青睐,出任了吏部满尚书, @赫一时。在“张煊案”中,张煊“上疏论陈名夏十罪二不法”弹劾,因谭泰极力庇护,陈名夏不但无罪,反而应该反坐张煊诬告之罪。最后谭泰就因擅权乱政、阿附多尔衮被处死,福临曾有旨不追究与谭泰有牵连的人,只是革了陈名夏的官,品级俸禄照旧,发正黄旗汉军下与闲散官随朝。
但是陈名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文人性格弱点,“好为名高”、“性锐虑疏”、恃才凌人,四面树敌,口无遮拦,得罪一片。在复审“张煊案”中, 洪承畴“招对俱实”,获得了皇帝的宽恕。而陈名夏却“厉声强辩、 闪烁其辞,及诘问辞穷,乃哭诉投诚之功”,让福临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感慨“其为辗转矫诈之小人也!”狡辩、装哭,对于马背上的满族人来讲,最为看不起了。顺治皇帝放了他一马,但已经成为“定时炸弹”!
历史上许多人都知道“ 兔死狗烹”的道理,张良、 范蠡,以及明朝开国元勋 刘伯温等等,都知道远离庙堂,隐于江湖。陈名夏在朝代更替之时,处于政治的漩涡。特别是明末南北党之争,在清朝继续延续,“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 阉党 冯铨在明朝之时就与 东林党人明争暗斗,还有宁完我,都在伺机寻求报复。陈名夏 信口开河,自己找死,对宁完我说:“只须留头发、复 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宁完我马上弹劾他行事叵测、 结党营私、纵子行贿等多条罪款。
敌人在暗处,对手在找茬,陈名夏自己还不知道,或者 粗心大意,没有政治头脑,被人利用。
特别是在此之前的“任珍案”。顺治十年二月,福临复命陈名夏署理吏部尚书。皇帝福临认为尽管任珍“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却“曾立大功”, 言外之意,似乎是示意群臣应酌情轻判。会集九卿科道会议重审此案,最后满汉会议的结果却不仅让福临失望,更让他愤怒。九卿科道各衙门的满洲官员都同意刑部原判,以出言不轨等罪判处任珍死刑。而陈名夏等二十七位汉官却认为,对于 婢女控告的罪行,任珍都不承认,“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陈名夏回答皇帝说,任珍不承认婢女的指控,如果根据此告辞定罪,他肯定不服,所以说恐开展辩之端;但是他确实负恩犯法,刑部原就拟定死罪,这就是应得之罪;可是又律无正条,似乎应该勒令他自尽。福临被这种 首鼠两端、 模棱两可的言辞彻底激怒了,福临趁势将众汉官狠狠训谕了一顿,指责他们不与满官 和衷共济, 拉帮结派、欺君妄为、 文过饰非,并命令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六部郎中齐集 午门外,马上议罪,刻不容缓。讨论的结果是陈名夏等三人应处死刑,另外二十四人分别应被流徙、革职、免职和降调。福临再一次放过了陈名夏,只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罢署吏部事。陈名夏等二十七位汉官坚持不同满官同议。皇帝要救人,陈名夏却不罢手,本来因为““张煊案””,已经放过他一马,现在“任珍案”又表现不好,对于一个满族的皇帝,尽管 口口声声要满汉一家,在关键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满族的利益以及皇帝的威严,顺治皇帝六岁登机,好不容易等到多尔衮去世,十四岁亲政反击,但是由于剃发、圈地、投充、逃人引起的各种反抗矛盾,加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母亲对自己婚姻大事的干预等等,都有可能导致顺治皇帝的多心猜疑,对满汉大臣互相倾轧的不满。
即使这样,顽劣而又独断的顺治皇帝还是放了陈名夏一马。也是基于当时大清入关不久,政治不稳,农民起义之火继续燎原,南明政权存在。
少年天子曾经在十一年正月十一日警告陈名夏:“与其才高而不思报国,不如才庸而思报国之为愈也。倘若知而不思报效,擅敢 卵形,事发绝不轻贷,彼时勿得怨朕,自贻伊戚耳。” 党首陈名夏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或许一些察觉,但是还继续他文人的本性,因为明朝之时,言官宁肯被处死,但长期受儒家传统教育,也要主持自己所谓的“正义”,有些 一根筋。
陈名夏与 方以智、 阎尔梅三人在明清易代之中虽然政治选择不同, 但并没有导致他们背弃相互之间的友情。可见,他也是一个懂得朋友之情的人。
宁完我发难,福临亲自讯问了陈名夏,可见当时的局势,皇帝需要杀人,杀个猴子已儆百官。陈名夏极力为自己辩白。福临又遍召群臣,突临内院,让侍臣当众宣读宁完我的劾奏,陈名夏不等侍臣读完,就逐条反驳宁完我的指责,福临大怒道:“即使要辩解,为何不等宣读完毕?”于是命九卿汇集左阙门,环坐会审,陈名夏跪着与宁完我对质,只承认说了“留头发复衣冠”的话。吏部等衙门与议政王大臣等先后两次在内殿审讯陈名夏,都认为宁完我劾奏陈名夏诸款属实,应该论斩。十二日,福临令改斩为绞。可以看出,此事蓄谋已久,皇帝要杀人,还怕找不到借口?宁完我和顺治等群臣要了一处好看的戏,最后发了一点仁慈,该斩为绞。文人陈名夏成了政治漩涡的棋子和牺牲品。
汤若望写到:“他(顺治)内心忽然间起一种狂妄的计划,而以一种青年人们的固执心肠,坚决施行。如果没有一位警告的人乘时刚强地加以谏止时,一件小小的事情,也会激起他的暴怒来,竟致使他的举动如同一位发疯发狂的人一般……”看来,高高在上的皇帝顺治心理有些扭曲了,由信天主教最后走向了信佛出家了。
福临倡导 忠孝忠义,希望满汉一家,相互制约,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大清的延续绵长;陈名夏死后,许多人又弹劾与其有关的事与人,亲戚和 党羽,皇帝阻挡,直言“以后论人论事,只许指实直言。不许再借陈名夏亲戚、党羽进奏。”可以看出,陈名夏死的何其冤枉?毕竟,顺治皇帝他是赏识陈名夏的学问,曾经向冯铨夸赞起陈名夏,说:“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冯铨回答说:“陈名夏于举业似所长。余亦易见。”福临沉默了一会儿,说:“陈名夏终好。”文人只不过在皇帝的眼中,是一枚棋子而已。
钱谦益与 柳如是, 龚鼎孳与顾 横波,在明末清初,每个文人选择了自己不同的生活道路,无可厚非。龚鼎孳“惟饮酒醉歌, 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安。”陈名夏喝酒大笑,清高疏虑,这是文人的特点和为官的弱点。文人就是文人,如果自视清高,和 杨修一样 恃才放旷,只落得被杀头;忠孝礼仪,爱国守家,修身齐天下,这是最基本的,但是盲目地陷入到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应该头脑清醒些。不值得去死,生命的意义在现实中很伟大。政客就是政客,文人就是文人,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和生存法则,文人心无 城府,切不可 妄自尊大,还应有自己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