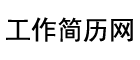达拉斯·斯麦兹的个人简介
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alker Smythe,又译斯迈思、史迈兹、斯密塞)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加拿大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他开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建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批判学派。他是将学术分析、政策研究和行为参与结合为一体的典范。其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
人物经历
求学期间:
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 Smythe)1907年生于加拿大,侯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受业,1928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斯麦兹在学校里专心研究经济史和理论史,他对政府工作报告和文件很感兴趣,认为它们提供了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重要条件。美国政府对1890年经济崩溃的听证会文献和有关交通行业的文件,构成了他博士论文的基础。毕业后的11年,斯麦兹一直在美国政府工作。在华盛顿的经历使他获得了应用社会科学的广泛经验。
初入社会:
1937年斯麦兹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到美国政府农业部、劳工部任政策分析员,使用并评估中央统计局的统计结果,同时,他开始与报纸和邮电等交通、通讯行业的工会打交道。在农业部和劳工部,他接触到要求改良的进步党人,包括政府公务员和工会领导人。与工人的合作使他对工人阶级的状况及其社会政治理想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获得了关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行业垄断巨头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亲身感受到传播行业劳动力变化的过程――由于新技术的影响,传统上需要掌握特殊技能才能就业的无线电和电话工人的技术优势日渐消失,他们开始感到非熟练工种对他们的职业冲击。斯麦兹也亲身体会到这些公司中激进的和保守的两种工会之间在支持工人斗争方法上的分歧。
进入FCC:
1943年,斯麦兹被任命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首席经济学家,对广播电视和电信政策发表建议和意见,直到1948年。美国的1934年《通讯法》将所有与电子传播有关的行业都归并FCC管理。斯麦兹去FCC讲解传播行业劳工关系争议及其对策,并对电信费率提供咨询建议。他希望,通过加入FCC,帮助这个独立法规行政机构行使职能,影响FCC制订和实施针对通讯和传播垄断的各项控制对策。他说,新政时期的FCC是一个可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地方。在FCC,斯麦兹指导了对广播电视政策的研究。当时FCC正忙于分配电波频率,斯麦兹参与了这项工作,并从商业利益集团捍卫私营者对广播电视控制权的运动中获得很大的教益,从而影响到他后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他对媒介商品化的认识不能说与他这一段的经历无关。任期即将结束时,他撰写了《对常规广播电视的经济学研究》,还为FCC经典性的《广播电视持照者的公共服务责任》(又称“蓝皮书”)撰稿。由于这些建议引起争议,最终被束之高阁。
来到Illinois:
1948年,斯麦兹离开FCC,来到新成立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创设了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的博士班,因而可以被称为传播学的摇篮。许多知名学者曾在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逗留,包括著名传播心理学家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传播批判学者格伯纳(George Gerbn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席勒(Herbert Schiller)。斯麦兹在传播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同时在商学系担任经济学教授。
斯麦兹的第一项研究检验了收看电视对家庭生活和闲暇时间的影响。在那个时期,电视刚刚进入美国人民的生活,正可以进行媒介介入前后的对照比较。斯麦兹采用的是实证研究方法,具体做法采用访谈法(用的是那个时代仅有的钢丝录音机)、日记法,和其他一些研究工具。虽然这一研究结果是供内部使用的,没有公开发表过,但却由此导致他指导美国教会组织对广播电视影响进行的同类研究。在50年代初期,由于非美活动调查造成的肃杀气氛,斯麦兹发现,只有教会内部还有足够的言论自由。斯麦兹一直对公共广播电视的问题有兴趣。他将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用于对电子媒介的研究。他为美国教育广播工作者联合会(NAEB)担任研究部主任,他的研究成果用于NAEB的院外活动和1950年末~1951年初FCC关于电视政策的听证会举证。那次,教育电视台和非商营电视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957年,他还作为加拿大皇家弗勒委员会的成员,对加拿大广播电视的政策、内容和效果进行了研究。应该说,斯麦兹对传播的研究,早期集中于广播电视和电子传播媒介。此时,他开始了对“受众商品理论”(audience commodity thesis)的研究。斯麦兹曾提到,他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思想是在1951年,他是在瓦萨(Vassar)学院消费者联盟研究所的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出的。当然,这一著名的思想经过多年的补充、发挥和完善。
回到故土:
1963年,斯麦兹全家做出了重大的决定――移居加拿大,回到他的家乡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市。席勒接替了他在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教席。然而,1969年,席勒发表了著名的《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议,校内的保守派对席勒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于是,席勒也离开了。其后,斯麦兹的一个主要学生古拜克(Thomas Guback)完成了他对国际电影业作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出色博士论文,并继承其导师衣钵,延续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伊利诺伊大学的传统。
斯麦兹回到加拿大后,在里贾纳的萨斯喀彻温大学任教。在里贾纳的10年,斯麦兹继续对受众商品问题的研究――他指出,受众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1974年,他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与制度政治经济学学者麦勒迪(William Melody)一道工作。此时,斯麦兹更加清晰地显示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特色,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电子传播的政策、受众商品论及加拿大传播业的依附状况。他完成了主要学术著作――《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1981),那是对决定加拿大传播依附性的垄断资本作辨证分析的经典之作。如今,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是加拿大传播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对加拿大电子传播研究方面的重要基地。
这段时期,斯麦兹参与加拿大政府和各种专业委员会的咨询活动,出席关于传播问题的各种听证会,作为专家,他的研究常常导致媒介结构的改变。他还到处旅行。斯麦兹在美国的天普(Temple)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到过智利、中国、日本、英国和东欧国家。所到之处,他影响了一批学者。他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派,培养了年轻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他的影响泽及几代:包括稍后的席勒、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最终,斯麦兹在西蒙·弗雷泽大学退休。1992年9月6日,他以85岁高龄去世。
两度访华:
斯迈思两度访华。
第一次是在“文革”期间,于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受加拿大艺术理事会资助访问中国。通过观察中国现实、访问相关负责人、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并结合当时第三世界广泛开展的现代化实践以及美国现代化范式遭到的广泛质疑,形成了他的报告《自行车之后是什么》(After Bicycles, What·)。报告在他生前并未公开发表,他只是希望报告能作为来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位“家庭成员”的善意批评,因而通过外交渠道转给了中国高层。此文的复印稿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界流传甚广。
第二次访华则是再度向西方打开大门的1978年,来到开放伊始的上海。当时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发展道路已经朝消费资本主义转型。
学术贡献
受众商品论: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化的社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广告费支持的大众传播媒介也自称是商业媒介。那么,这种大众媒介及其传播商业所提供的商品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人认为,商业广播电视的商品是标价出售的广告时段,这是从销售角度出发的;也有人认为,是电台播出的各种节目,这是从生产角度出发的。
但是,斯麦兹指出,广告时段的价值是传播产生的间接效果,而广播电视节目则是“钓饵”性质的“免费午餐”,它们都不是广播电视媒介生产的真正商品。早在1951年,他便提出,商营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是受众的人力(注意力),由此奠定了其后他的受众商品理论。1977年他发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一文,标志着受众商品理论的形成,引起了批判传播学领域的热烈辩论,并成为批判传播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分支。
根据斯麦兹对广告驱动性大众传播商品形式的研究,节目在广播电视中也许是有趣的,更经常是有用的部分;但大众媒介生产的消息、思想、形象、娱乐、言论和信息,却不是它最重要的产品。它们都像20世纪出售啤酒的小店通常采用的方法一样,是“免费午餐”这种“免费午餐”是用以吸引顾客登门饮酒的。以广告费支持的电视媒介提供的“免费午餐”是喜剧、音乐、新闻、游戏和戏剧,目的是引诱受众来到生产现场――电视机前。此时,测量受众的公司便能够计算他们的数量多寡,并区分各色人等的类别,然后将这些数据出售给广告者。媒介则根据“产品”(受众)的多寡和质量(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等人口指标)的高低(也就是购买力的强弱)向广告客户收取费用。所以,媒介公司的使命其实是将受众集合并打包,以便出售。这便揭示了商业广播电视的真正商品――尽管是临时形成的商品――受众群体。它解释了广播电视时段具有价值的原因、广告客户和媒介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商业受众测量机构存在的理由,从而将媒介行业的本质牢牢地置于经济基础上。毫无疑问,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具体运用。
这种与“常识”大相径庭的观点一经出现,有如空谷足音,立即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触发了学者对受众的关注,并成为批判研究者研究媒介经济流行的思路。
斯麦兹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时间都是劳动时间。由此,他得出了下面在常人眼中看来更加惊人的结论:“免费午餐”的享用者不仅仅是消磨时光,他们还在工作――他们在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是通过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的。其不公平处在于:受众在闲暇时间付出了劳动,为媒介创造了价值,但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反而需要承担其经济后果。这样的观点骇世惊俗;但这是对商业广播电视、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的商业广播电视独特风景进行的极为醒目的分析。
然而,正如马克思本人一样,斯麦兹的分析也被批评为庸俗政治经济学,批评者说他的观点将意识形态降低为经济基础,同时,将能动的人降低为无生命的被动商品,是经济决定论。一些持“积极受众”观点的学者,特别是提出“使用―满足”理论的学者,更是以大量的实证研究,竭力证实受众是主动参与媒介传播和意义创造的生产者,而不是产品。
笔者认为,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深刻地揭示了广播电视媒介传播的某种本质,但仅仅是一个方面――经济的本质。尽管这种本质是最重要的方面,但是,对传播这种复杂的人类活动,学者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范式进行不同的解释的。斯麦兹的学生和后继者也发展了“受众商品论”。例如,有人提出,受众不仅仅是在工作,他们也在娱乐。他们在付出劳动(出场)和经济(购买)代价的同时,也确实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特别是情感的慰藉,思想的交流,陪伴的作用等。
在诸多补充性的解释中,莫斯考书中的“控制性商品”(cybernetic commodity)的概念最发人深省。莫斯考引证了米汗(Eileen R. Meehan)以接收率等信息服务机构的产品为中心的商品观点。米翰认为,广播电视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实际的受众(所谓受众的人头数),而只是关于受众的信息(观众的多少、类别的构成、使用媒介的形态)。媒介与广告客户之间的交易,是通过收听收视率行业进行的商品交换,而由这种交换过程产生的商品,是收听收视率这种信息性、资料性商品,而不是有形的商品。收听收视率调查公司从事的,是这种信息的检测过程。
传播政治经济学:
斯麦兹与加拿大传播研究的先驱殷尼斯(Harold A. Innis)一样,认为经济制度和传播体系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传播的流动对经济的发展是关键的因素。传播是各种经济力量的核心。他“始终坚持,毫不动摇地倾全力于分析媒介制度及其与深层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体系的联系。”
斯麦兹坚信传播在信息经济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他提出,“传播是世界所有矛盾聚集的焦点”
他认为,对社会过程,特别是对技术的考察,应该置于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对传播和媒介行为的考察,也应如此。传播是重要然而常常被学者忽略的盲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架构中的盲点。此言既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引起轩然大波,斯麦兹受到非难。特别是,斯麦兹还对传播学研究有自己的独特想法。
1954年,斯麦兹发表了《对传播理论的观察》(Some Observations on Communication Theory)一文。这篇文章是对传播研究方法论的探讨,1953年先是以意大利语发表在意大利刊物上,其后才以英文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抨击了传播学研究中“逻辑实证科学理论的”方法,主张一种“制度历史理论的”途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传播学实证主义研究的权威人物克拉珀(Joseph Klapper)。
所谓“逻辑实证科学理论”是以自然科学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来要求社会科学,用经验观察来建立有规律的理论体系,其要素是由反证的命题组成的。在早期,斯麦兹并不反对经验调查的方法,他自己还进行过一些实证调查。但是,40年代以后,传播学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政治学的民意调查方法,越来越趋向于行为主义的社会学、心理学,而放弃了历史哲学等思辩性的研究方法和对社会制度的宏观考察。随着这种研究越来越趋向数量化和微观化,斯麦兹便越来越反感“对所观察的行为作简约的、证伪的陈述,从而使智力活动的丰富性降低”这种经验主义。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对理论和行为之间的辨证关系作广阔的历史分析,将其置于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较大框架中,进行批判、付诸实践。面对来自“科学”的挑战,他说:“在证实了我可以做逻辑实证科学理论式的u2018科学u2019之后,我很高兴地永远抛弃了它”。
斯麦兹的后人继续对行为主义方法进行批判。行为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研究至今仍是传播学方法论的两大主要分歧流派,尽管行为主义式的研究结论已经不像初期那样简单和绝对了。
主要著作
《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Blind spot of Western Marxism)1977年。
《对传播理论的观察》(Some Observations on Communication Theory)1954年。
文章《自行车之后是什么?》(After Bicycles, What·)1973年(中文版刊于《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Capitalism,Consciousness,and Canada,1981)1974年。(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