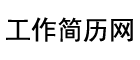范升的个人简介
范升,字辩卿,生年不详,卒于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东汉代郡(今山西代县)人。他是东汉初年较为著名的经学家。
儒生范升
范升字辩卿,代郡(今河北省阳原县)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为议曹史。时莽频发兵役,征赋繁兴,升乃奏记邑曰:“升闻子以人不间于其父母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为忠。今众人咸称朝圣,皆曰公明。盖明者无不见,圣者无不闻。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则元元焉所呼天?公以为是而不言,则过小矣;知而从令,则过大矣。二者于公无可以免,宜乎天下归怨于公矣。朝以远者不服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为重忧。今动与时戾,事与道反,驰鹜覆车之辙,探汤败事之后,后出益可怪,晚发愈可惧耳。方春岁首,而动发远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谷价腾跃,斛至数千,吏人陷于汤火之中,非国家之人也。如此,则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县,免元元之急,不可书传,愿蒙引见,极陈所怀。”邑虽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称病乞身,邑不听,令乘传使上党。升遂与汉兵会,因留不还。 建武二年,光武征诣怀宫,拜议郎,迁博士,上疏让曰:“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并耆艾qíài (古以六十岁为耆,五十岁为艾。泛指老年人)经学深明,而臣不以时退,与恭并立,深知羌学,又不能达,惭负二老,无颜于世。诵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开口以为人师,愿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许,然由是重之,数诏引见,每有大议,辄见访问。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升退而奏曰: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CA75倦之听。孔子曰:“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夫学而不约,必叛道也。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谓知教,颜渊可谓善学矣。《老子》曰:“学道日损。”损犹约也。又曰:“绝学无忧。”绝末学也。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诗》、《书》之作,其来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观,至于如命,自卫反鲁,乃正《雅》、《颂》。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已。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万事理。”《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以下博士。
著名的经学家范升
范升,字辩卿,生年不详,卒于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东汉代郡(今山西代县)人。他是东汉初年较为著名的经学家。 范升幼年时丧失父母,生长于外祖父家中。他喜好读书, 9岁时就能通晓《论语》、《孝经》。长大后,就专门研究《易经》和《老子》,并以教授生徒为业。范升所研究的《易经》,是西汉宣帝时由梁丘贺这个人传下来的,所以称为《梁丘易》。 范升的青年时期,正处于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宁的时期。其时,青徐一带的农民起义已经发展蔓延,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但王莽政权还在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大批征发兵力,攻打周边少数民族。另一方面,为了标榜自己的贤明,还在不断笼络文人学士。故此时范升被王莽政权的大司空王邑征用,引为汉曹史,辅佐王邑制定政策。范升很了解全国的局势,曾专门写了一份意见书,指出当时的危险不只来自外族,而主要来自国内,所谓“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他指出,当时全国的形势已是田地荒芜,粮价腾跃,吏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反抗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他奉劝王莽政权迅速改弦更张,并以十分急切的心情,表示要亲自见到王莽,陈述自己的意见。但利令智昏的王莽政权非但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反而认为他在危言耸听,遂把他送上巡视地方的车子,将他送到上党,说是让他到那里巡视。其时,刘秀的起义军已经占领上党,范升遂留在了起义军中。 因为范升枉当时有一定的学术声望,而且颇懂政治,所以东汉建立以后设立经学博士时,他与粱恭等人被刘秀立为《易经》博士。他很谦虚,认为自己比粱恭年轻,又不比粱恭经学深明,曾上疏要求更换他人。刘秀因此更看重他,多次下诏引见, “每有大议,辄见访问。” 自西汉以来,一些懦生就以讲经为名,把自然界出现的一些怪异现象与人事的安危祸福联系起来,用经学的条文加以解释论证,后人有称这种懦术为“天人之学”的。这种风气,在齐地尤盛。特别是对于《易经》的讲究,更把它当作占卜未来吉凶安危以及重大政治变动的卦书来看待。刘秀建立后汉后,不少儒生就大言吹嘘,说这是他们早已予料和推断出的事情。刘秀虽然不信这种胡说,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很推崇这种君权神授的现点,所以,到东汉时期谶纬之学更盛行起来。刘秀还企图把一些专门研究“天人之变”的易学以及与此有关的其它经学抬高到至尊的地位,在中央为之设立博士员位。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正月,尚书令韩歆上疏,请求为《费氏易》、《左氏春秋》设立博士,刘秀在背后支持,下诏让当时的公卿大夫、博士们讨论。所谓《费氏易》,是指西汉齐人费直所传的易经,是以《易经》来占卜筮问的专门学问;至于《左氏春秋》,即左丘明的《左传》,在当时亦被有人当作占验政治变动的专学。对于这个建议,范升坚持反对意见,他与韩歆、太中大夫许淑等人展开激烈辩论,至“日中乃罢”。他认为,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在他看来,《左传》是左丘明对于春秋重大事件的解释,违背了孔子褒贬之大义,是不能当作圣经来看待的。至于《费氏易》等类,则更属经学异端,根本乙不可登大雅之堂。这是他公开提出的理由。实际上,他从刘秀巩固统治地位的利益出发,有着更高的考虑。在这场辩论之后,他就专门给刘秀上了一封奏章,说明他反对多立经学博士的真正用心。他认为,刘秀痛疾学术的衰微,用心于学术,务求广见博闻,这种用心是良苫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求广而不求精,势必引起诸家竞起,争取自己的官学地位,会使杂七杂八的东西充斥其间, 长久争论不休。到那时,听从这些非正统学问的议论,就会失道,如果不听从他们的议论,那就会失人,将会进退维谷,“恐陛下必有厌听之倦”,难以驾御这种局面。他反复奉劝刘秀,说刘秀“草创天下,纲纪未定,”“奏立《左》、《费》, 非政急务”;要刘秀向汉武帝学习,“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正其本末,方可治理万事。他的劝告,终于使刘秀觉悟,放弃了广立经学博士的打算。 从范升的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死啃经书、食古不化的书生,而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相当敏锐的政治见识。他善于观察分析形势,也有足够的应对之策,这是他能够受到刘秀的重视和礼遇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从汉武帝把儒学抬到独尊的地位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一种统治思想。这种思想,以讲求忠孝仁义为本,以孔夫子的传教为经,在统治阶级中逐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背离了这些经训,那就会使封建统治的秩序发生混乱,政治思想的统治就会动摇。从西汉后期以来,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十分重视经学的本源和师传,不使异端学说混杂。范升不愧为明智的儒生,他认为,只有讲《诗》、《书》,修礼乐,才是政之急务,而广立博士,只会搞乱人们的思想,防碍东汉政权的巩固。正是从封建政治思想统治出发,他针对一些人以司马迁多用《左传》为由,请立《左传》博士的议论,专门举出司马迁违戾五经,背谬孔子的言论,以及左传误解《春秋》的例子,对这种议论加以反驳。这也说明他多么注意和用心于东汉政权的思想统一。 范升毕竟是一位儒生,他大概明于辨事,而不熟悉实际。汉明帝永平年间,他曾出任聊城县(今山东聊城县)县令,很快就被免职。不久,死在家中。但在中国儒学发展史和政治思想史上,他还有一定的地位。 后升为出妻所告,坐系,得出,还乡里。永平中,为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