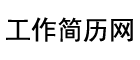董秀玉的个人简介
1941年生,上海人。1956年进入人民出版社,1979年任《读书》编辑部副主任,1986年担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1987年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3年回北京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4年创办《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创办“韬奋图书中心”。工作经验
经验一发展战略的确定,真是一个企业发展最为重要的第一步。
当年在联合出版集团,交代任务后就放手让你去搏。三联当时在地下室画出“一机两翼”的发展蓝图:以本版图书为中心、打开通道、发展期刊群,这是面对现实、把握趋势后的系统思考,也是整合资源的策略把握,更是大家团结奋斗的方向和凝聚力。为以后的发展明确了目标。这个时代,面对竞争剧烈的市场经济,没有目标的过一天算一天,瞎猫碰死耗子,是没有希望的。
经验二团队的培养。人是竞争力的第一要素,创新的基础。出版事业必须依靠团队合作才能做出优秀成绩。
三联队伍的素质很好,虽然负荷重、压力大,但始终努力乐观、团结正派。三联的编辑从来没有利润指标的压力,但选题被批准之难也是众所周知的。要求不但是好书,还必须适合三联文化特色,必须可以长销;选题应该创新、有市场空间又不同质。这要求编辑关心市场,多读书多交朋友多思考,心志要高眼界要远。我们给了一些条件,如内部培训、鼓励参与各种学术研讨活动,活跃选题讨论会等,但总的说还是系统培养少,创新机制也不够。
现在不少出版社作跨学科、跨媒介的员工系统培训计划,在总的发展战略上的不断创新,给干部员工实战的锻炼和教育,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根本工作。
经验三守住文化尊严,扎根品牌形象。这是我上任北京三联后不断在谈,并坚持实践的根本问题。
1993年初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界,一直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两种功能的巨大混乱中拉锯。启发知性的出版物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而商业利益亦是企业发展必备的动力。出版者必须在不断抗拒一元化及平庸化的压力中,紧跟时代与社会,寻求持续的突破和发展。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他的出版物,他的事业发展,就是出版人的追求和理念的写照。”
1994年,我在“总编辑新年献辞”中发表《留住尊严》,强调出版作为文化产业,必须坚守文化尊严,通过不断增长实力去引领市场。
完全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守住文化的尊严何尝不是品牌的基础。哪一家著名的大出版公司会没有方向、不管不顾的乱出书?又有谁把自己的招牌掰碎了随便卖?只有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的博弈中运转自如、具长远战略眼光、守得住根本,不断积累、强化自己品牌,才会拥有最多的忠诚读者,才真正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三联为什么做金庸?这个问题好。首先,品牌的积累应该是多元的,三联当时的书刊是“分层一流(小众、中众、大众均要求一流)”的结构模式,我认为金庸小说可以进文学殿堂,是大众读物中的一流作品。我从香港回来时,其他武侠小说大家的作品也拿得到,但不敢拿。我得守紧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中形成的三联品牌。由于合作方式的原因,发行量虽大,我们的利益并不大,我还是接受。因为流动资金量大,光这一套书,每年现金流几千万,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企业极为重要(93年我接手时全年销售总码洋才711万)。但我经营时也极为小心,从不让它上订货会。因为每次订货会的货款有限,订了金庸就很难再订别的。我不上,书店只能订本版书,保证了我的根本,金庸则随要随添,不影响销售。这样,即使金庸撤走,我也不会受太大影响。事实上,十年后的版权转移,真对我们没影响。
经验四政绩、面子重要,还是企业的长远利益重要。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问题最大。政绩、面子还连着位子票子,衡量起来难度就大了。
我在三联干过一些傻事,但自己想想还是值。
先是盖楼,因为土地面积极小(2000平米),后面又是居民楼怕挡光,只能盖两层。后来变成个斜坡形的四层(三层3/4,四层1/2)。可这地点实在太好,盖这么点房真不甘心。遂决定挖两层地下室(这可得多花不少钱)。再捉摸,按发展规划,我们有机会买下那居民楼,那我们这楼就可以长高,十层没问题,于是决定打下十层的地基,以后长高就不必推倒重来了。当然,这更得多花钱。这就挺傻。
房盖成,想开书店,从传统或发展看,都应开。全体员工也支持。于是最好的楼下两层加最大的地下一层交书店,全社只得挤进那1/2的四层里,员工大统间,领导小小间。有领导笑我们,舒服的大办公室不要,开什么书店?傻不傻!
《三联生活周刊》起起落落反反复复,好不容易到99年开始赢利,2000年继续赢利,仍是双周刊。几年下来期刊格局大变,周刊纷起。“生活”如不及时改周刊,一定优势尽失;而要改刊更是大难,一是又需资金的大投入,二是又会有1-2年的亏损期。原来的合资经营方不干,需另找资金投入,原有的合作方又不甘心,封砸了办公室,打起了官司。我一面找资金,一面打官司,同时还必须在不动用出版社一分钱的情况下(我答应过社委会办周刊不花社里一分钱)把周刊转过来。那一年我真是疯了似的忙,而那一年我已经应该退休了。关心我的朋友说,“你傻不傻,不转,你这块账是赢利;转了,账是赤字。你几十年做得辛辛苦苦漂漂亮亮,为什么退休了还非要弄成这样一张成绩单?”我说,“不会啊,我手里的广告可以保证最多两年后一定赢利,而且一定是大利。”“两年后,那会是你的成绩吗?”我哑然。但想来想去,这是必须的选择。就算我傻吧。
最后,就傻到底吧。为了让后任不要有太多负担,我清库房、理坏账,尽可能在任上把这些从我账上清掉,使利润从2001年的上千万元尽量下调。财务说这样对以后的发展会好,我同意。其实,只要做了应做的事情,成绩单如何,对我来说真不重要。
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傻,但在企业的长远发展利益面前,我觉得还是傻一点为好。
这些,是我那十年在北京三联做的、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些基础工作。审计小组和集团有关领导也肯定了这些工作的扎实。但那真还只是个起步,只有在这些基础工作上继续改革创新和不断调整,才能实现三联的真正飞跃。
后三联时代2002年,我打的退休报告被批准,9月正式退休。我在57岁的时候就给署里打过报告,希望上来新人(也举荐了具体的年轻人),自己退二线。这样有个共同工作期,有较长的沟通与交流,对企业发展有利。署里认同这想法,但还是难以实施。其实,事业就像滚滚长河,一浪推一浪,新老的及时更替很重要,新鲜的血液为企业带来更强劲的生命力。
我交得干干净净就出去开会、玩儿了。以后就一直忙,倒是困绕我20年的严重失眠,退休一个月后居然不治而愈,真是我的大开心。
我离开后,三联确实发生了很多事,包括起伏和波折,我没什么话好说,只希望三联好。我对三联从来有信心。
《我们仨》是我退休后编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我知道会畅销,但没想到那么畅销。一开始我估计起码可印20万,可最后卖了70多万册。杨先生用她的全部感情在写,读者也用心在读,这种心和感情的深入交流真是太难得了。
是的,按照三联现在的规矩,编辑是有提成,但我退休了,大概就不能算他们的编辑了吧。我没想这么多,只是觉得这书应该是三联的,我离开了,就算是送给三联的一份礼物吧。
现在我当着工作室的顾问,又组织和参与着几个国际性的年会,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自己喜欢的书。我觉得很充实、很开心,真有做回我自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