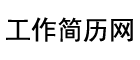陈企霞的个人简介
陈企霞自由撰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世纪的中国文坛曾有两大冤假错案,一个是“胡风反党集团”案,在就是“丁、陈反党集团”案。丁是丁玲,陈就是陈企霞。陈企霞在延安时代就和丁玲同事,解放初期,二人又共同主编《文艺报》,后陈企霞又担任《民族文学》月刊主编。
简介
陈企霞 (1913-1988) 文学评论家。原名陈延桂,浙江鄞县人,著名作家、文学家。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小商家庭,自幼生活贫困。曾在免费的宁波甲种商业学校读书。1925年入宁波甲
陈企霞种商业学校。1927年离开家乡外出流浪,当过银行练习生,布店店员和其他杂工。因为爱好文学,1931年始发表小说、散文,次年至上海,在通信中认识叶紫,到上海共同创办无名文艺社,出版过《无名文艺旬刊》和《无名文艺月刊》。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革命活动。
1933年在《无名文艺旬刊》发表第一篇小说《梦里的挣扎》。次年在《文学季刊》一卷四期发表的小说《狮嘴谷》是他早期较好的作品。此外也写过评论文章。但数量不多,一直未结集出版。一生的主要贡献在文学编辑和文学教学方面。1940年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协助丁玲编《解放日报》副刊,参加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1945年参加华北文艺工作团,华北文工团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后,任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主任,参与编辑《北方文化》(成仿吾主编)、《华北文艺》(欧阳山主编)等刊。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联副秘书长、文协秘书长,不久又于丁玲、萧殷一同编《文艺报》,任《文艺报》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协第二、四届理事。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5年因“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被错划为“右派”。后任杭州大学教师。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后调北京任矛盾文学奖评委,《民族文学》杂志主编。1987年离休,1988年1月16日病逝。
作品
著有论文集《光荣的任务》;
小说《狮嘴谷》、《第一个碾米厂的毁灭》、《星夜曲》等;
作品收入《企霞文存》。
趣闻
好酒
陈企霞好酒,在他生命最后几年,老伴儿为其身体考虑,禁了他的酒,他就长年和老伴儿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手段极为高明,不管老太太如何实施三光政策,老头儿每天早上一睁眼,总能从床底下捞出个酒瓶,咕咚就一口。
偷懒的父亲
陈企霞太性情了,给子女起名字特别偷懒,老大出生在延安,就叫陈延安,依此类推,解放后在北京生了孩子,就叫陈北京。可是后来一直在北京定居,陈北京的妹妹出生了,家人犯了难,问陈企霞该叫啥,他说还不简单,就叫陈幼京嘛。
陈企霞与“匿名信”事件 陈企霞是所谓“丁、陈***小集团”里的主要人物。
匿名信事件
丁玲陈企霞集团冤案“丁、陈”受批判的直接原因是***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该信指斥主编《文艺报》的丁玲、陈企霞拒绝发表李希凡和蓝翎评论《红楼梦》的文章,是“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1954年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了这封信。自此,作协党组便多次召开会议,展开了对《文艺报》的批判。这时候,一些曾被《文艺报》批评过的人,有了名正言顺发泄不满的借口,正如周扬所说,“有冤的申冤,有仇的报仇。”
陈企霞之子陈恭怀在《关于父亲的〈陈述书〉》一文中说:“解放初期的文艺界,尽管有当年解放区文艺创作的雄厚基础和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指引,但是,一方面在文艺理论和批评上深受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及批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从《文艺报》创刊到1955年前后,文艺界上层领导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直是相当激烈的,抗战以前文艺界在上海的矛盾也不时重新流露。《文艺报》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和批评的阵地,自然就成为矛盾的焦点。所以《文艺报》的工作就不断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指责。”
那么,夹杂着一系列恩怨的批判,让性格耿直、心高气傲的陈企霞难以忍受,可在批斗会上根本没有他申辩的机会。于是,一封反映作协党组处理问题不公的匿名信发出了。
对于匿名信的具体情况,几位当事人的纪录在一些细节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综合起来才可能得到最接近真实的过程。
张僖先生在其所著《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中披露:
大约是1954年11月或12月,正是中国作协批判检查《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时候,有一天,刘白羽同志找到我,递给我一封信说:“这是封写给刘***同志的匿名信。***同志批下来了,转给了***部,又转到咱们这里,让查一下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
我接过信,这是一个普通的短白信封,没有单位落款,更不是作协通常用的那种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刘***同志亲启”的字样。在刘***的名字上画着一个圈,估计是刘***同志圈阅过。信的投寄地点是北京西单某邮局。
我印象中信封里面有三四张普通稿纸,上面也没有印刷单位。
……从信中的内容和措词来看,写信的人对作协内部的情况非常熟悉,给人的初步印象是,这封信是作协内部的知情人写的……
既然是刘***同志亲自批下来的,当然事关重大。我马上找到***部六局局长陈中,他说已经知道这件事,写信的人可能就在中国作协内部。他希望我们自己先查一下。
我们根据匿名信的笔迹开始查找……我们从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档案中,取出每个人自己填写的登记表,把表上的字迹与匿名信一一核对。然而找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这件事放在工作日程上大约有一年之久。(因为陈坚决不承认,又没有有力的证据。)
……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巴人)找到刘白羽、严文井和我,讲述了一件事情,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女编辑,这次她在与副主编楼适夷的谈话中,揭发出当年匿名信的事。说是当时陈企霞写了信,通过这个女编辑找了一个“老秀才”,把这封信抄了一遍,然后陈企霞去了上海,由这个女编辑把信寄出的。
我们当即去了这个女编辑的家。女编辑领着我们又找到了那个替陈企霞抄信的“老秀才”,最后证明女编辑说的是事实。
陈企霞同志可能是得到了消息,第二天,他就由他的夫人郑重陪着来到作协,拿出一把钥匙交给我们说:“这就是罪证。”这把钥匙是那个女编辑家的……匿名信的问题到此真相大白……1957年8月3日陈企霞被迫在作协党组的第十次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他承认了匿名信的事件……
那么,这封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陈恭怀说:“这封匿名信向中央反映了对作协党组某些人在处理《文艺报》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信中说,去年(1953年)年底党对《文艺报》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是由于文艺界某些领导同志推卸责任,中央“偏听偏信”的结果。作协党组对《文艺报》的批评“过火”了,是“随波逐流”、“看风使舵”、“趁火打劫”。
而写这封信的女编辑同陈企霞又是什么关系呢?陈企霞的学生徐光耀在2005年4月接受凤凰卫视访谈时,谈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天津的女作家柳某揭发了陈企霞。陈企霞在作协党组会上有一个“坦白交代”,“他一上去就说,我是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我就是个***分子,我陈企霞。这个自以为很聪明,办了很多***的事,实际上,我还是不聪明的。他就说,我跟周言已经同居了10年,我们有一个密室,这个密室的钥匙,我现在掏出来交给组织。就把钥匙掏出来扔在桌子上。大伙儿就觉得,哎,姘居10年这样的丑事他承认了,钥匙交出来了。这个匿名信是他跟周言秘密地写好了,写好了以后,让周言的一个侄女给写出来什么的。”而徐光耀发表在《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上的《昨夜西风凋碧树》长篇回忆文章,对此事作了如下记载:“他所交代的u2018比柳某所谈更可怕u2019的第一件事,是与一个女人姘居10年,二人合伙写过3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
张僖与徐光耀对同一件事情的说法有3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一是这位女编辑的名字。张僖和徐光耀一开始都没有说出来,明显有道德上的隐晦意图。而实际上,陈企霞在自己的检查中面对着参加会议的几百人,是说出了女编辑的名字的。正是陈企霞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丁玲的极大反感,以至于两人被“解放”之后,几乎不再来往。到2005年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徐光耀先生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再加隐晦,何况采访者是凤凰卫视,毕竟在内地的观众面要少得多。
二是笔迹为谁所留。张僖说是一个“老秀才”,徐光耀说是女编辑的侄女。
三是匿名信的数量。张僖只提到了刘***批示的一封,徐光耀明确说是3封。
其中,对于破案具有重大意义的笔迹线索,竟然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抄写者,一个是“老秀才”,一个是女编辑的侄女,这期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陈企霞为了避免人们对自己的怀疑,在他出差上海期间,那位女编辑在北京寄出了匿名信。即使如此,匿名信所反映的问题,仍然使人们将怀疑的目光聚焦在陈企霞身上。只是因为笔迹对不上,陈企霞又坚决否认是其所为,事情才拖了下来。
在1955年8月至9月作协党组的一系列扩大会议上,白朗在一次发言中说,她在1954年12月曾以支委身份找陈企霞谈过一次话。当她1955年6月下旬第一次看到那封匿名信时,就感觉到信中的话语同陈企霞的谈话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并当即向领导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白朗的发言引出了其他与会者的一些证据,证明陈企霞与匿名信有关,因为不仅信中的思想观点与陈企霞相一致,而且信中所提供的事实只有陈企霞全部知道。据此推测,匿名信是陈企霞与人合作共谋,由别人抄写寄出的。
而在作协党组会召开前的7月底,正在安徽梅山水库体验生活的陈企霞就接到了周扬、刘白羽通知他回京与会的电报。这样的揭发是不是会前“布置”好的不敢枉猜,但通过匿名信来揭批陈企霞则是无疑的。
对于会议的情景,陈企霞在《陈述书》中写道:
1955年8月1日夜, 我按照来电的要求抵达北京,1日晚即参加了党组扩大会上关于匿名信问题的讨论。第一次会主要是文艺报几个同志的发言,他们一致认为信是我写的。会后,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同志留下我来同我谈话,我申辩了一下,并提出一些意见。我向周扬同志说,不能把很多不明不白的事情,强加在(我)头上……我希望弄清各种事实。周扬同志回答我说:你就是这样说也是错的……最后。周扬同志又说,你看,今天晚上大家一起来检举你,该不是布置的吧?我当即回答他说:如果是正确的思想斗争的话,不但可以布置,而且也是应当布置的。问题是斗争得对不对,不在于是否经过领导的布置。这以后,又继续开了二次党组扩大会,空气愈来愈紧张,所有所谓“揭露”的问题,已使我不能辩白,我在向组织上写了一次书面报告后,就不让参加这样的会了。在我所参加的最后一次的会上,同一个在去年中宣部会上提出要检查文艺报方向路线却没有丝毫结果的张光年(即光未然)同志提出要停止我的党籍,审查我的历史,党内公布我的问题。他并(此处有两字不清)说去年讨论红楼梦时他曾向周扬同志提议要在党内公布我的材料,周扬没有照办,所以陈不承认错误云云。8月19日晚上,我被宣布逮捕(有逮捕证),搜查了住所,但始终并未宣布是犯的什么罪。我当场说了这样三句话:这样的决定是根本错误的,完全把范围搞乱了。康濯、张僖两位同志(他们是带来捕人的)你们以后检查要深刻些。我是服从政府法令,才勉强就捕。
这以后,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还使我莫名其妙的被迫丧失自由的生活,到1956年5月22日为止,共计9个月零3天。
1955年下半年,陈企霞被秘密隔离审查,囚禁于东总布胡同22号院内一个隐秘的角落,逼迫其交代现实和历史“问题”。即由追查匿名信,进而怀疑其与王实味相牵连,有“托派嫌疑”。
蒋祖林在《回忆母亲丁玲――1957年前后》中,记述母亲丁玲的话:“1953年春天,我辞去了所有的行政工作,专事创作。1955年4月,我去无锡,住在梅园,写作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7月,回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时已开始了反u2018胡风***集团u2019的斗争,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8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有六七十人参加。一个月内共开了16次会。前三次会是为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匿名信,认为是陈企霞所写,并肯定有合谋者,但陈企霞不承认是他写的。从第四次会议,斗争的矛头就转向我。”
关于丁、陈的问题,作协党组前后召集了16次党组扩大会议,最后向中央写出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他们“***”活动的四大“罪状”: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 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经中央批示,丁、陈的罪名就定下来了。
1956年,国内的政治形势转为宽松。5月,因为“托派嫌疑”而被***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被释放。加之,丁、陈不断申诉,到了1957年上半年,大鸣大放已是如火如荼,中宣部复查小组重新审查后,对已作出的结论予以否定,以周扬为首的文化部门也放出了向丁、陈道歉的空气。6月6日,整风鸣放的末期,作协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也相继发言。有的说,“丁、陈***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接着,党组扩大会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周扬,批评得越来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强烈。
由此,陈企霞在作协党组的肃反总结会上,情绪激愤,语含嘲讽地说:“作协肃反的成绩是什么?好比将一根根好端端的木头烧光了,指着剩下的一小堆木炭说,看,这就是我的成绩!”这时的陈企霞对自己的遭遇奋力抗争。
然而两天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随着反右斗争的风起云涌,作协党组的道歉便烟消火灭,局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转变成针对丁、陈的批判大会。陈企霞和丁玲的申诉,不再是要“澄清真相”,而是“向党猖狂进攻,是翻案”,并被定义为“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果”。会议规模也一再扩大,与会人数达到几百人。
1957年7月25日,作协党组再一次召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周扬等对“丁陈***集团”的评价和口吻完全改变了。周扬除了肯定对“丁、陈***集团”的批判没有什么错误之外,还历数了丁玲和陈企霞在南京、在延安的历史问题。在此情况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女编辑揭发说,陈企霞是匿名信的主谋。
几乎是同时,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天津的一位女作家也坦白了关于丁、陈的一些问题。
8月3日,在中国作协党组的第十次扩大会上,陈企霞说出了一句震惊与会者的话:“首先我要揭露匿名信的事和还有比柳溪所说的更可怕的事――”他随即承认了匿名信的事件,交代了生活问题,还交代了与丁玲丈夫陈明在汽车站碰头等建立“攻守同盟”的情况。
陈企霞在8月3日坦白之前,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对此,陈恭怀在《盛世的灾难――忆父亲陈企霞》中有一番沉痛的描写:
这天(指7月25日)晚上他开会回来,神态忧郁,精神委靡,一改过去不愿在母亲面前谈论工作上事情的常态,很伤心地对母亲说:“我现在很可能过不了关,党组扩大会议文艺界各方面的人都来了,有200多人,会上你一句我一句逼得很紧,压力很大。丁玲过去在南京被捕变节的事,组织上从未说过,我一点也不知情,平常也没有听她谈起过,现在众口一词,断定她那段经历有问题,根本不听她的分辩。说我们是***小集团,实际上是我们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背后谈论过他,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意见没有经过组织,有些自由主义,我是有些责任的。现在他们攻击我的最主要问题是匿名信,矛头都指向我。匿名信实际上是某某搞的,我以前对她说过一些情况,她认为我是冤枉的,就写成匿名信向中央反映。她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作协尽管对我所有的学生和要好的朋友都核对过笔迹,也没有查出来。反映事实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用匿名信的方式。我虽然没有让她写,可她这样做我也是有很大的责任的。我现在只有把这件事说清楚,才能减轻我的罪责。我考虑再三,觉得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组织讲清楚。但我现在也很为难,过去我顶得那么厉害,会议拖得那么长久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我坚决不承认。如果我现在去说明真相,怎么说得出口呢?即使我要去讲,他们会不会相信呢?”
母亲劝父亲不要顾虑大多,说,你既然要向组织靠拢,就要打消一切不必要的顾虑,还是自己主动去讲好。其他有什么都可以讲,不应该回避,要相信党,相信组织。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
有关匿名信,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细节:女编辑是用左手写的。而丁玲的说法是:“陈企霞在会上交代,承认那封匿名信是他写的,找人抄的。”通过对匿名信不同说法的对比,笔者认为抄写者是一位“老秀才”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毕竟此说的作者张僖曾是处理匿名信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但徐光耀匿名信有3封的说法是一个细节补充。很可能“老秀才”抄了一封,女编辑左手写了一封,另一个人又抄了另一封。最基本的,匿名信的发起者是陈企霞,具体执行者是周言应是无疑的。
仅仅4天,即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集团》的文章,行动可称神速。
紧接着,在8月11日《文艺报》也发表长篇通讯《文艺界反右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集团阴谋败露》。
面对超过1955年的巨大压力,陈企霞的精神垮塌了。于是,他坦白说自己是匿名信的幕后主使,甚而连自己私生活中的问题也向组织一股脑儿地作了交代,他期望能获得“彻底坦白”的效果。可一旦突破了这条精神底线,他再揭发丁玲等人也就没有了心理上的道德障碍。至此,所谓“丁、陈集团”的主将丁玲,在陈企霞缴械之后,又一次从批判者中神奇地置换为被批判者。
其后,中央发布指示:“右派应该下去劳动改造,接近工农兵。”于是,陈企霞被赶到了河北唐山的柏各庄农场。1959年,陈企霞要求离开农场。经作协党组同意,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接收”陈企霞前去任教。在教学岗位上,他“夹起尾巴”、勤勤恳恳工作了20年。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仍遭受了非人的劫难,痛苦更10倍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
1979年,加在他头上的冤案终于平反。落实政策后,全家重返北京,他也回到了文学工作岗位上。但岁月风霜的严酷,强逼着他走向了迟暮。他虽然受邀参加了被称为“新时期春天”的第四次文代会,但他似乎感觉不到春天的气息,病体支离,步履蹒跚,寡言少语,表情漠然,当年性格倔强、言语锋利的陈企霞随着青春的消逝,彻底散淡到无影无形了。
精神垮了,创造力死了,只剩下肉体的存活和日常的烟酒消乏解闷。1988年,痛苦中的陈企霞终于辞别了这个扰攘的世界。
人物评价
陈企霞企霞老是位资深作家,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联,同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转入共产党。1940年到延安,在社长博古领导下,协助丁玲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抗日胜利后,他到华北联大文学系担任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随部队进京,先是在周扬和沙可夫领导下筹备全国文代会,会后马上投入了筹办《文艺报》,《文艺报》创刊后担任副主编。因为主持编务及日常工作,他经常忙得废寝忘食,虽说累些,倒也心情舒畅。可是做梦都不曾想到,因为工作上的某些分歧,到1955年12月竟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他不服,又是抗议,又是上《陈述书》,1956年6月中宣部终于宣布“u2018丁、陈反党集团u2019不能成立,给丁、陈摘去u2018反党集团u2019帽子”。天真的陈企霞以为一切都雨过天晴了,还自责不该一度有那么大的委屈情绪。可是不到一年,他又成了右派分子。右派问题改正后,一些跟他资历能力不相上下的人,都比他地位高,他分配到《民族文学》担任主编。有人说他的职务安排低了,他听了冷冷一笑:“陈企霞有什么了不起?把持一个刊物,权力够大了。”知道底细的人则揭他的老底:“谁叫他爱抗上?”
人们说的“抗上”,实际上,也就是爱“较真”。企霞先生为人耿直,襟怀坦荡,遇事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敢于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有时与领导人意见相左,也敢于摆实事讲道理。建国之初第一次文代会刚开完,大会党组开会总结工作,企霞是党组秘书。不知周扬听了谁的汇报,说从河北调来的马少波住房没安排好,因此就给陈企霞扣上一顶“故意违抗命令”的帽子。当时文艺界调进京的人不少,一时很难都安排得周全。企霞讲了实际情况,解释了几句,周扬就拍着桌子嚷道:“你这算什么共产党员!”要是别人,领导发火了,不再言语也就罢了。企霞不行,他觉得那么大的领导,怎么一点修养也没有?便针锋相对地责问周扬:“你这算什么领导?”所谓的抗上,不外乎就是这一类的“较真”。
有人说,陈企霞脾气大,不好接触,其实不然。1981年我到文学讲习所学习,陈企霞是我的校外导师,我每两周去他家一趟,请他辅导。这一年跟他接触最多了。我也是个直肠子,他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有时就冒犯他几句,老头从不生气。比如他生病了,单位的同事买点水果看望他,他不但不接受,还把人家轰出去。我说他:“太不近人情了!”他疑惑道:“有那么严重吗?”他要求编辑部对作者来稿必须做到“每稿必复”。我说他这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他故作吃惊状地一笑:“要是那样,今后还是先抱西瓜吧。”
那时,陈企霞刚从杭州调回北京不到一年,家住在团结湖中国作协家属宿舍,居住条件不好,他总是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无人打扰的小屋接待我。两根“烟囱”,你递一枝,我递一枝,吞云吐雾,把屋子的氛围倒也熏染得很是融洽。
他几乎不看我的作品,也不大听我谈读书体会,告诉我少听课,多逛街,多聊天。既然学习上没多少谈的,有时我就扯到反右后发配到大西北的一些事儿,他总是摆手:“不说那些事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再说有什么意思?”
我说:“过去了,也得有个是非,你陈企霞搞u2018独立王国u2019了吗?搞u2018反党小集团u2019了吗?”
他说:“周扬同志已经认错了,他在四届文代会上当众讲的,你们都听见了的:u2018陈企霞同志有什么问题?只不过他与我有不同意见,我就把他打成了反党集团、右派分子。我现在诚恳地向他赔礼道歉。u2019人家认错了,你不能得理不让人啊。”
何等豁达!这是一种胸怀。我知道企霞老打成右派后,很快被送到农场劳动改造,从行政10级的工资骤降到只发26元钱的生活费,夫人郑重被开除党籍,带着儿女下放到福建乡下的水利工地,子女们受尽了歧视与污辱,弟弟及一些学生、朋友都受到株连。那么多苦难,只一句“赔礼道歉”就统统宽容了。这个一向“较真”的人,在个人得失上,又一点也不“较真”了。
陈企霞传陈企霞从杭州回到北京时已经68岁,身体瘦弱,行动迟缓,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些。有一天我见他心情很好,就劝他:“你的经历见证了我国文坛两代人的坎坷遭遇,应该写点东西留给后人。”
他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可写的?你不是也经历了吗!”
他不愿意多谈自己,尤其不愿意谈论个人的冤屈,对我说“别总舔自己的伤口”。但是他对中国文坛上的三个人却念念不忘,几次说想为他们写点东西,替他们述说当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记述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他们是王实味、丁玲、萧军。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都是经陈企霞之手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后来批判这些文章时,要追究责任,多亏博古同志挡驾,他说:“文章都是我签发的,要追究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博古同志挺身而出,使陈企霞免遭了一场劫难。听企霞老说了这件事,使我对博古的人品也有了新的认识。
卸下了心灵的重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企霞老本想把憋了二十多年的劲头都拿出来,可是时代变了,他的身体也不给他做主,往往力不从心,加之他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也常有不适应之处,单位上的事情也不省心,所以“不如意事常八九”,晚年的心境并不舒畅。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仍然有所彷徨,这正像他在一首诗中所吟咏的:
我曾向大海谈论小溪
大海对我咆哮
怒斥我:“看它不起”
我曾向小溪描述海洋
小溪对我讪笑
嘲弄我:“荒诞夸张!”
这一个要讳言自己来历
那一个不想知自己去处
我彷徨无地,自认是笨拙糊涂
愿你日日夜夜怒涛汹涌
愿你年年月月细水长流
我无能于巧语花言而背弃真理